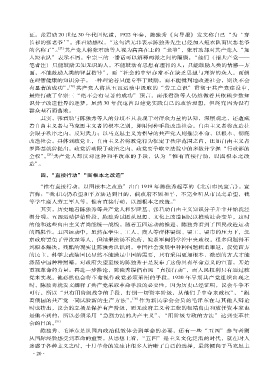Page 20 - 201902
P. 20
证。张君劢 20 世纪 30 年代回忆道,1922 年春,陈独秀 《向导报》发文称自己 “为 ‘穿
长衫的张老爷’”。张君劢感叹,“这句话无非表示陈独秀先生已经加入短衣队而厌恶老爷
的名称了”。 共产党人将张君劢等人视为高高在上的 “老爷”,张君劢却对共产党人 “加
〔 27〕
入短衣队”表示不屑。牟宗三的一番话可以解释两派之间的隔膜,“他们 (指共产党———
笔者注)只能鼓励无知无识的人,不能鼓动有思想有理智的人;只能鼓励人类的情感一方
面,不能鼓励人类的智慧指导”,而 “社会的中坚亦常不在缺乏思想与理智的众人,而倒
在理智健康的知识分子。一种理论若只能专事于鼓励,而不能批判地改进社会,则决不会
有显著的成功”。 共产党人将从五四运动中汲取的 “劳工意识”贯彻于共产党建设中,
〔 28〕
最终打破了牟宗三 “绝不会有显著的成功”预言,而张君劢等人仍然做着只依赖少数知
识分子改造世界的迷梦,虽然 30 年代也曾以建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但终究因为没有
群众基石而落败。
其实,张君劢与陈独秀等人的分歧不只表现于对群众力量的认知,深层观之,还蕴藏
着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之别,即用何种手段改造社会。自由主义者将改造社
会限于秩序之内,反对武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则推崇革命,以根本、彻底
改造社会。具体到政党上,自由主义者将政党行为框定于秩序范围之内,比如自由主义者
罗隆基就曾提出,政党活动限于政治之内,政党要争取立法院中的多数并掌握 “行政部的
全权”。 共产党人却反对这种和平改革的手段,认为 “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
〔 29〕
造”。
四、“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出自 1919 年陈独秀起草的 《北京市民宣言》。宣
言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到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
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其实,历史地看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和罗隆基、张君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非开始就泾
渭分明。五四运动伊始阶段,陈独秀试图从思想、文化上改造国民以推动社会变革,这时
的他和这些自由主义者尚能统一战线。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陈独秀看到了国民改造运动
的局限性。五四运动中,虽然在学生、工人、商人等群体罢课、罢工、罢市的压力下,北
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等人,但结果换汤不换药,皖系军阀仍掌控中央政权,很多问题得不
到根本解决。残酷的现实让陈独秀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中种种问题积重难返,仅凭西方
的民主、科学去武装国民显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只有采用更加根本、激烈的方式才能
涤荡中国种种黑暗。对政府失望至极的陈独秀于是发布了这份具有革命意义的宣言,开始
重视革命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论,陈独秀提倡市民 “直接行动”,而人民权利只有通过政
党来实现,他必然也会将革命视作政党必须采用的手段。1920 年早期共产党组织出现之
时,陈独秀就发文阐释了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的必要性,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议会斗争不
可行,所以 “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跟
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 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在与其他人辩论
〔 30〕
时也指出,议会的立场是保护有产阶级,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极端自由和放任资本家也
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采用 “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达到变革社
会的目的。
〔 31〕
陈独秀、毛泽东是从国内政治低效体会到革命的必要,还有一些 “五四”参与者则
从国际经验感受到革命的重要。从思想上看,“五四”是主义文化泛滥的时代,就在时人
迷惑于各种主义之时,十月革命的发生让很多人清晰了自己的选择,最终倾向于马克思主
0 ·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