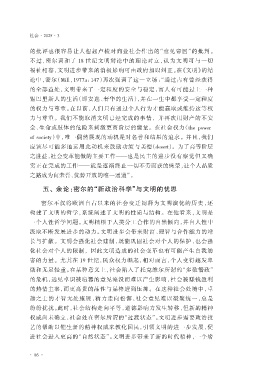Page 93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93
社会·2025·3
的批评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卢梭对商业社会作出的“意见帝国”的批判。
不过,密尔调和了 18 世纪文明辩论中的理论对立,认为文明可与一切
福祉相容,文明进步带来的消极影响可由政府加以纠正。在《文明》的结
论中,密尔( Mill,1977a:147)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通过占有曾经获得
的全部益处,文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与稳定,富人有可能过上一种
锡巴里斯人的生活(即安逸、奢华的生活),并在一生中都享受一定程度
的权力与尊重。 在以前,人们只有通过个人行为才能赢取或维持这等权
力与尊重。 我们不能取消文明已经完成的事情, 并再次用财产的不安
全、生命或肢体的危险来刺激更高阶层的能量。 在社会权力( the power
of society)中,唯一偶然展现的动机是对名誉和结果的追求。 并且,我们
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此动机来鼓励功绩与美德(desert)。 为了高等阶层
之进益,社会变革能做的主要工作———也是民主的进步没有察觉但又确
实正在完成的工作———就是逐渐终止一切不劳而获的殊荣,让个人品质
之路成为向荣誉、优势开放的唯一通道”。
五、 余论:密尔的“新政治科学”与文明的忧思
密尔不仅将欧洲自古以来的社会变迁阐释为文明演化的历史,还
构建了文明的哲学,系统阐述了文明的性质与结构。 在他看来,文明是
一个人性哲学问题。 文明植根于人类分工合作的自然倾向,并自人性中
汲取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 文明进步会带来财富、理智与合作能力的增
长与扩散。 文明会强化社会建制,既能巩固社会对个人的保护,也会强
化社会对个人的限制, 因此文明造成的社会变革也有可能产生自我妨
害的力量。 尤其在 19 世纪,民众权力崛起,相对而言,个人变得越发卑
微和无足轻重。在某种意义上,社会陷入了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僭政”
的危机,远见卓识被喧嚣的意见淹没而难以产生影响,社会被赚钱盈利
的热情主宰,而更高贵的品性与品格遭到压抑。 在这种社会处境中,卓
越之士的才智无处施展,精力走向松懈,社会意见难以凝聚统一,总是
纷纷扰扰。此时,社会结构走向平等,道德影响力发生转移,但新的精神
权威尚未确立,社会处在密尔所谓的“过渡状态”。文明进步需要政治技
艺的帮助以催生新的精神权威来教化国民,引领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促
进社会进入更高的“自然状态”。文明进步带来了新的时代精神,一个崭
·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