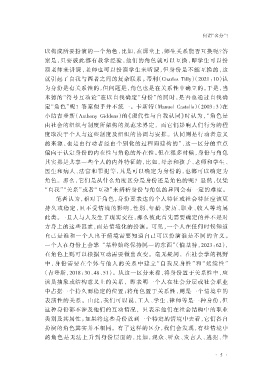Page 12 - 《社会》2024年第6期
P. 12
何谓“名分”?
以构成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比如,在课堂上,师生关系能否互换呢?答
案是,只要彼此都有教学经验,他们的角色就可以互换,即学生可以扮
演老师来讲课,老师也可以扮演学生来听课,但身份是不能互换的,这
就引起了自我与两者之间的复杂联系。 蒂利( Charles Tilly)(2021:10)认
为身份是有关系性的,但问题是,角色也是在关系性中确立的。于是,当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在以自我确定“身份”的同时,是否也通过自我确
定“角色”呢? 答案似乎并不统一。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2003:3)在
小结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时认为,“角色是
由社会的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 而它们影响人们行为的程
度取决于个人与这些制度及组织的协调与安排。 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
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这一区分的重点
偏向于认定身份的内在性与角色的外在性。 但在很多时候,身份与角色
其实都是共享一些个人的内外特征的,比如,母亲和孩子、老师和学生、
医生和病人、法官和罪犯等,凡是可以确定为身份的,也都可以确定为
角色。 那么,它们是从什么角度区分是身份还是角色的呢? 显然,仅凭
“自我”“关系”或者“互动”来辨析身份与角色的异同会有一定的难度。
笔者认为,相对于角色,身份要表达的个人特征或社会特征应该更
持久或稳定,且不受情境的影响,性别、年龄、资历、职业、收入等均属
此类。 一旦人与人发生了现实交往,那么彼此首先需要确定的并不是对
方身上的这些因素,而是情境化的扮演。 可见,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知道
自己是谁和一个人出于情境需要知道自己可以扮演谁是不同的含义。
一个人在身份上会靠“某种始终保持同一的东西”(伯基特,2023:62),
在角色上则可以根据互动需要做出改变。 毫无疑问, 在社会学的视野
中 ,身 份 需 要在个体 与 他 人 的关系中 建 立“自 我 反 身 性 ” 和“延 续 性 ”
(吉登斯,2018:30、48、51)。 从这一区分来看,将身份置于关系性中,应
该是抽象或结构意义上的关系, 即表明一个人在社会分层或社会职业
中占据一个持久而稳定的位置;将角色置于关系性,则是一个情境中的
表演性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说,工人、学生、律师等是一种身份,但
这种身份都不涉及他们的互动情况, 只表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职业
类别及其属性。 如果将这些身份放到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去看,它们各自
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相同。 有了这样的区分,我们会发现,有些情境中
的角色是无法上升到身份层面的,比如,观众、听众、发言人、逃犯、肇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