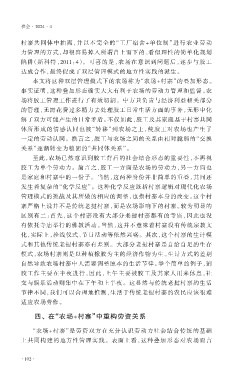Page 109 - 《社会》2024年第4期
P. 109
社会·2024·4
村寨共同体中抽离,并以不完全的“工厂宿舍+单位制”进行农业劳动
力管理的方式,却很容易掉入所谓自上而下的、看似理性的简单化规划
陷阱(斯科特,2011:4)。 可喜的是,农场在意识到问题后,逐步与胶工
达成合作,最终促成了双层管理模式的地方性实践的诞生。
本文将这种双层管理模式下的农场称为“农场+村寨”的叠加形态。
事实证明,这种叠加形态确实大大有利于农场的劳动力管理和监督。 农
场将胶工管理工作进行了有效切割, 中方只负责与经济利益相关部分
的管理,无需花费过多精力去处理胶工日常生活方面的事务,无形中化
解了双方可能产生的日常矛盾。 不仅如此,胶工及其家庭基于村寨共同
体所形成的情感认同也被“转移”到农场之上,使胶工对农场也产生了
一定的劳动认同。 换言之,胶工与农场之间的关系由相对脆弱的“交换
关系”逐渐转变为稳固的“共同体关系”。
至此,农场已然意识到胶工背后的社会结合形态的重要性,不再视
胶工为单个劳动力。 简言之,胶工一方面是农场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
是家庭和村寨中的一份子。 当然,这两种身份并非简单的重叠,其间还
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 这种化学反应既指村寨逻辑对现代化农场
管理模式的挑战及其所做的相应的调整,也指村寨本身的改变。 这个村
寨严格上说并不是传统老挝村寨,而是农场影响下的村寨。 较为明显的
区别有二:首先,这个村寨没有大部分老挝村寨都有的寺庙,因此也没
有依托寺庙举行的佛教活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村寨没有传统宗教文
化,实际上,拴线仪式、节日活动等依然兴盛。 其次,这个村寨的生计模
式和其他传统老挝村寨亦有差别。 大部分老挝村寨是自给自足的生存
模式,农场村寨则是以种植橡胶为主的经济作物为生。 生计方式的差别
自然导致农场村寨中人需要调整原本的生活节律。 举个简单的例子,割
胶工作主要在半夜进行,因此,上午主要被胶工及其家人用来休息,社
交与娱乐活动则集中在下午和上半夜。 这显然与传统老挝村寨的生活
节律不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生活于传统老挝村寨的农民应该很难
适应农场劳作。
四、 在“农场+村寨”中重构劳资关系
“农场+村寨”是劳资双方在充分认识劳动力社会结合传统的基础
上共同构建的地方性管理实践。 表面上看,这种叠加形态对农场而言
·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