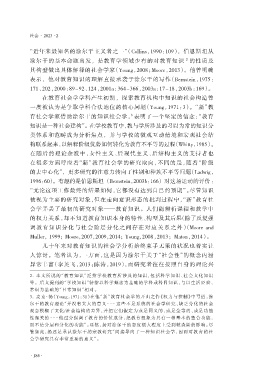Page 193 - 《社会》2023年第2期
P. 193
社会·2023·2
“近年来最知名的涂尔干主义者之一”(Collins,1990:109), 伯恩斯坦从
2
涂尔干的基本命题出发, 是教育学领域少有的对教育知识 的性质及
其构型做出具体解释的社会学家(Young,2008;Moore,2013)。 他曾明确
表示, 他对教育知识的理解直接承袭于涂尔干的写作( Bernstein,1975:
171、202,2000:89-92、124,2001a:364-366,2003a:17-18,2003b:169)。
在教育社会学学科产生初期, 探索教育机构中知识的社会构造曾
一度被认为是争取学科合法地位的核心问题( Young,1971:3)。“新”教
3
育社会学家借助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 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教育
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 在学校教育中,教与学所涉及的习以为常的知识分
类体系和范畴成为分析焦点, 并与学校的微观互动情境和宏观社会结
构联系起来,以解释阶级优势如何转化为教育不平等的过程(Whitty,1985)。
在随后的理论余波中,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支持者也
在很多方面呼应着“新”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不同的是,随着“阶级
的去中心化”, 更多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性别和种族不平等问题( Ladwig,
1996:60)。 有趣的是伯恩斯坦(Bernstein,2003b:166) 对这场运动的评价:
“无论这项工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它都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尽管知识
被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在走向意识形态的批判过程中,“新”教育社
会学弄丢了最初的研究对象——教育知识。 人们能辨析课程和教学中
—
的权力关系,却不知道教育知识本身的特性、构型及其后果(除了反复强
调教 育 知识 分 化 与 社会阶 层 分 化 之间存 在 对 应 关 系之外)(Moore and
Muller, 1999; Moore,2007,2009,2014; Young,2008,2013; Maton,2014)。
几十年来对教育知识的社会学分析始终束手无策的状况也着实让
人惊讶。 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是因为涂尔干关于“社会性”的概念内涵
异常丰富(李英飞,2013;陈涛,2019),而研究者往往按照自身的理论兴
2. 本文所说的“教育 知识”泛指学校 教育所 涉及的知识,包括科学 知识、社会文化知识
等。 后文提到的“学校知识”特指以科学概念为基础的学科或科目知识,与以生活经验、
常识为基础的“日常知识”相对。
3. 麦克·扬(Young,1971:31)在他“新”教育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权力与控制》中写道,涂
尔干的教育理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些不是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缺乏分化的社会
观念模糊了文化/社会结构的差异,并把它们假定为或是同义的,或是全等的,或是功能
性相关的……他过分强调了教育的价值成分,把教育想象为具有一种基本的整合功能,
而不是分层和分化的功能”。 显然,扬对涂尔干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帕森斯的影响。 尽
管如此,扬还是承认涂尔干的宗教研究“间接导向了一种知识 社会学 ,因而对教 育的社
会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