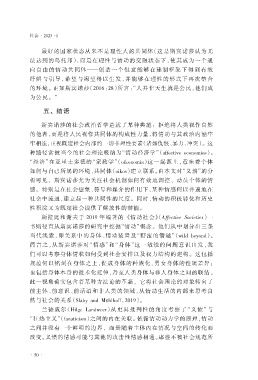Page 57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57
社会·2023·1
最好的国家状态从来不是理性人的共同体(这是斯宾诺莎认为无
法达到的乌托邦),而是在理性与情动的交融状态下,使其成为一个通
向 自 由 的情 动共同体———创造一 个 恨意能够在 建制框架下 得 到 有 效
纾解与引导,希望与渴望得以生发,并能够在理性的形式下再次整合
的环境。 正如斯宾诺莎( 2016:28)所言:“人并非天生就是公民,他们成
为公民。 ”
五、 结语
斯宾诺莎的社会政治哲学造就了某种典范: 拒绝将人类视作自然
的他者,而是将人民视作共同体的构成性力量,将情动与其政治内涵牢
牢相连,正视既定社会内部的一切非理性要素(诸如仇恨、暴力、冲突)。 这
种路径常被当今的社会理论吸纳为“情动经济学”( affective economies)。
“经济”在亚里士多德的“家政学”( oikonomia)这一起源上,意味着个体
如何与自己所属的环境、共同体(oikos)建立联系。由本文对“义愤”的分
析可见, 斯宾诺莎尤为关注社会机制如何有效地调控、 动员个体的情
感。 特别是在社会想象、符号和媒介的作用下,某种情感何以普遍地在
社会中流通,建立起一种共同性的尺度。 同时,情动的积极转化和历史
性积淀又为既定社会提供了解放性的潜能。
斯拉比和谢夫于 2019 年编著的 《情动社会》(Affective Societies)一
书则径直从斯宾诺莎的研究中挖掘“情动”概念。 他们从中划分出三条
当代线索,即关系中的身体、情动装置及“野蛮的僭越”(wild beyond)。
简言之,从斯宾诺莎对“情感”和“身体”这一敏锐的问题意识出发,我
们可以考察身体情状如何受到社会安排以及权力结构的建构。 这包括
规范何以铭刻在身体之上,促成身体的种族化、男女身体的性属差异;
也包括身体本身的技术化延伸,乃至人类身体与非人身体之间的联结。
此一视角确实包含着某种方法论的革新, 它将社会理论的对象转向了
前主体、前意识、前话语和非人类的领域,从情动生活的内部来思考自
然与社会的关系(Slaby and Mühlhoff,2019)。
兰德 威 尔(Hilge Landweer)从更 具 批 判 性的角 度 考 察 了“义 愤 ”与
“狂热主义”(fanaticism)之间的内在关联。 依循情动动力学的原理,情动
之间并没有一个鲜明的边界, 而是随着主体内在情况与空间的转化而
改变。义愤的情感可能与其他的攻击性情感相通。那些不被社会规范所
·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