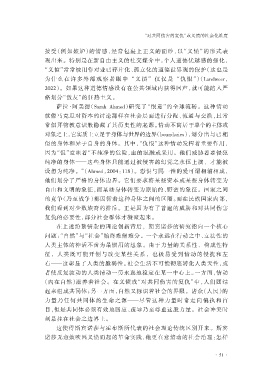Page 58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58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接受(例如嫉妒)的情感,经常包裹上正义的面纱,以“义愤”的形式表
现出来。 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交媒介中,个人道德优越感的强化,
“义愤”常常被用作对业已碎片化、孤立化的道德世界观的保护(这也是
为 什 么 在 许 多 外 部 观 察 者 眼 中 “义 愤 ” 仅 仅 是 “仇 恨 ”)( Landweer,
2022)。 如果这种道德情感没有在公共领域内获得回声,就可能陷入严
格划分“敌友”的狂热主义。
萨拉·阿美德(Sarah Ahmed)研究了“恨意”的全球流转。 这种情动
就像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那样在社会层面进行分配、流通与交换,且常
常似拜物教意识般隐藏了其历史性的起源。情动不寓居于单个的主体或
对象之上,它实质上立足于身体与世界的边界( boundaries),划分出与己相
似的身体和异于自身的身体。 其中,“仇恨”这种情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恨”意味着“不纯净的危险,血的混融或采用。 他们威胁着要侵犯
—
纯净的身体——这些身体只能通过被侵害的幻觉之永恒上演, 才能被
设想为纯净。 ”(Ahmed,2004:118)。 恐惧与同一性的爱可谓相辅相成,
他们划分了严格的身体边界。 它们要求将某些资本或某些身体转变为
自由和文明的象征,而某些身体转变为原始的、野蛮的象征。 国家之间
的竞争(乃至战争)都因循着这种身体之间的区隔。而在民族国家内部,
我们看到对少数族裔的排斥。 正是因为有了普遍的威胁和对共同伤害
复仇的必要性,部分社会群体才凝聚起来。
在上述纷繁错杂的理论创新背后, 斯宾诺莎的研究指向一个核心
问题:“自然”与“社会”始终难解难分。 一个永远在行动之中、立法性的
人类主体的神话不啻为最惯用的想象。 由于力量的关系性、 构成性特
征, 人类既可能开创与改变某些关 系 , 也 极 易受到 情动 的侵 扰 和 左
右———这彰显了人类的脆弱性。 社会生活不可能彻底转化人类天性,或
者使反复波动的人类情动一劳永逸地稳定在某一中心上。 一方面,情动
(内在自然)滋养着社会。 在义愤或“对共同伤害的复仇”中,人们团结
起来组成共同体;另一方面,自然又标识着社会的界限。 诸众(人民)的
力量 乃 任 何 共同体 的生命 之 源———尽管这 种 力 量 时常走 向 偏 执 和 盲
目,但是共同体必须有效地回应、疏导乃至尊重这股力量。 社会冲突时
刻悬挂在社会之边界上。
这使得斯宾诺莎与霍布斯所代表的社会理论传统区别开来。 斯宾
诺莎无意鼓吹因义愤而起的革命实践,他更在意情动的社会治理:怎样
·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