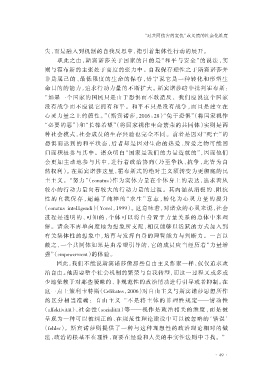Page 56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56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失,而是融入到机制的自我反思中,指引着集体性行动的展开。
职此之由,斯宾诺莎关于国家的目的是“和平与安全”的说法,实
则与霍布斯的主张处于高度的张力中。 自我保存理性之于斯宾诺莎并
非是属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命的保存,毋宁说它是一种转化和形塑生
命目的的能力,追求行动力量的不断扩大。 斯宾诺莎暗中批判霍布斯: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只是由于恐惧而不敢造反, 我们应说这个国家
没有战争而不应说它拥有和平。 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而且是建立在
心灵力量之上的德性。 ”(斯宾诺莎,2016:28)“免于恐惧”(将国家视作
“必要的恶”)和“长葆希望”(将国家视作生命繁荣的共同体)实则是两
种社会模式,社会成员的生存经验也完全不同。 前者是因对“死亡”的
恐惧而达到的和平状态,后者却是因对生命的热爱、所爱之物可能回
归而积极参与其中。 诸众明白“国家是我们的力量造就的”,因而他们
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其中,进行着政治协商(乃至争执、抗争,此皆为自
然权利)。 在斯宾诺莎这里,霍布斯式的绝对主义须转变为更彻底的民
主主义。“努力”( conatus)作为实体力量在个体身上的表达,追求着从
较小的行动力量向着较大的行动力量的过渡。 其内涵从消极的、阻抗
性 的 自 我 保 存 , 超 越 了 纯 粹 的“求 生 ” 意 志 , 转 化 为 心 灵 力 量 的 提 升
(conatus intelligendi)(Yovel,1999)。 这意味着,对诸众的心灵来说,社会
进程是透明的、可知的,个体可以将自身置于力量关系的总体中来理
解。 诸众不再单向度地为想象所支配,相反能够以活跃的方式加入到
有关集体性的想象中,培育与发挥自身的理智能力与判断力。 一言以
蔽之,一个共同体如果是由希望引导的,它的成员应当经历着“力量增
强”(empowerment)的体验。
因此,我们不能说斯宾诺莎像那些自由主义作家一样,仅仅追求政
治自由。 他需要整个社会机制的繁荣与自我转型,而这一过程又或多或
少地依赖于对那些暧昧的、非规范性的政治情动进行引导或者抑制。 在
这一点上策利卡特斯(Celikates,2006)对自由主义与斯宾诺莎思想所作
的区 分 相 当 准 确 : 自由 主 义“不 是将 主 体 的 非 理 性 规 定———情 动 性
(affektivit覿t)、社会性(sozialit覿t)等———视 作 是政 治相 关 的维度,而 是 被
呈现为一种可以被纠正的、在规范性理论建设中可以被忽略的‘错误’
(fehler)。 斯宾诺莎则提供了一种与这种理想性的政治理论相对的做
法,政治的根基不在理性,而要在经验和人类的事实性法则中寻找。 ”
·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