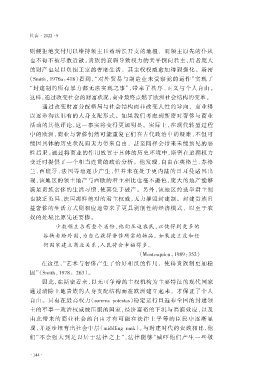Page 151 - 《社会》2022年第5期
P. 151
社会·2022·5
则便拒绝交付用以维持领主日益增长开支的地租, 而领主原先的仆从
也不得不被尽数遣散。 贵族的衰弱导致权力的天平倒向君主,后者庞大
的财产也足以负担王室的奢靡生活, 其主权权威愈加得到强化。 斯密
( Smith,1976a:418)看到,“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未受察觉的运作”实现了
“封建制的所有暴力都无法实现之事”,带来了秩序、正义与个人自由。
这样,通过改变社会的财富状况,商业最终点燃了欧洲社会结构的变革。
通过改变财富分配格局与社会结构而非改变人性的导向, 商业得
以逐步淘汰旧有的人身支配形式。 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密对奢侈与商业
活动的其他评论,这一事实将变得更加明显。 实际上,在现代转型过程
中的欧洲,商业与奢侈仍然可能重复它们在古代政治中的疑难,不但可
能因具体的历史状况而无力带来自由, 甚至同样会带来未能预见的恶
性后果。 通过将商业的作用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斯密在追溯权力
变迁时提供了一个相当连贯的政治分析。 他发现,自由在英格兰、苏格
兰、西班牙、法国等地逐步产生,但并未在处于更内陆的日耳曼诸国出
现,该地区的领主地产与西欧的君主相比也毫不逊色,庞大的地产能够
满足贵族奢侈的生活习惯,使其免于破产。 另外,该地区的选举君主制
也缺乏英国、法国那样绝对的君主权威,无力摧毁封建制。 封建贵族日
益奢侈的生活方式则相应地带来了更具剥削性的经济模式, 以至于农
奴的处境比原先还要惨。
少数领主占有整个省份,他们压迫农民,以便得到更多的
谷物卖给外国,为自己获得奢侈所需的物品。 如果波兰没和任
何国家建立商业关系,人民将会幸福得多。
( Montesquieu,1989:352)
在这里,“艺术与奢侈产生了恰好相反的作用, 使得贵族制更加稳
固”(Smith,1978: 263)。
因此,在斯密看来,以无可争辩的主权机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
通过清除土地贵族的人身支配结构而在欧洲建立起来, 才保证了个人
自由。 只有在最高权力(summa potestas)稳定运行且遍布全国的封建领
主的军事—政治权威被压服的国家,经济富裕的下沉与涓滴效应,以及
由此带来的商业社会的自由才有可能在法律 上 平 等 的臣 民 中 逐 渐 显
现,并逐步培育出社会中层(middling rank)。 与封建时代的贵族相比,他
们“不会强大到足以居于法律之上”,法律能够“威吓他们产生一些敬
·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