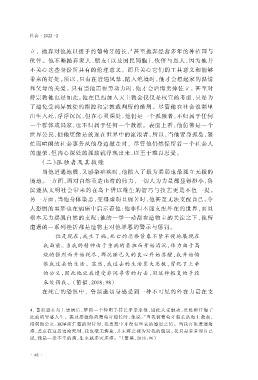Page 55 - 《社会》2022年第2期
P. 55
社会·2022·2
4
立, 抛弃对他施以援手的葡萄牙船长, 甚至抛弃经营多年的种植园与
伙伴。 他不断抛弃家人、朋友(以及国民同胞)、伙伴与恩人,因为他并
不关心这些身份所具有的伦理意义, 而只关心它们的工具意义和能够
带来的好处。所以,只有在遭遇风暴,陷入绝境时,他才会想起家的温情
和父母的关爱。 只有当他需要劳动力时,他才会后悔卖掉佐立。 甚至对
待宗教他也是如此。 他在巴西加入天主教会仅仅是权宜的考虑,只是为
了避免受到异教徒的指控和宗教裁判所的酷刑。 尽管他在社会浪潮里
出生入死,浮浮沉沉,但在心灵深处,他仍是一个孤独者,不归属于任何
一个群体或国家,也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教派。 表面上看,他仿佛是一个
世界公民,但他更像是放逐在世界中的流浪者。所以,当他置身孤岛,繁
忙而喧闹的社会事务从他身边撤走时, 尽管他仍然保留着一个社会人
的虚荣,但内心深处的孤独就浮现出来,以至于难以忍受。
(二)孤独者及其救赎
当他遭遇地震,又感染疟疾时,他陷入了最为柔弱也最孤立无援的
境地。一方面,面对自然重造山海的伟力,一切人为力量都显得渺小,鲁
滨逊从文明社会带来的在岛上借以维生的智巧与技艺更是不值一提。
另一方面,当他身体染恙,变得虚弱且痛苦时,他甚至无法支配自己。令
人恐惧的噩梦也在病痛中启示着他:他非但不能支配外在的世界,而且
根本无力摆脱自然的支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造物主的关注之下,他所
遭遇的一系列挫折都是造物主对他罪恶的警示与惩罚。
但是现在,我生了病,死亡的悲惨景象不紧不慢地展现在
我面前。 当我的精神由于重病的负担而开始消沉,体力由于高
烧的强烈而开始耗尽,那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我开始悔
恨我过去的生活。 显然,我过去的生活罪大恶极,冒犯了上帝
的公义,因此他让我遭受非同寻常的打击,用这种报复的手段
来处罚我。 (笛福,2018:98)
在死亡的恐惧中, 鲁滨逊切身感受到一种不可见的外在力量在支
4. 鲁滨逊在岛上患病后,梦到一个神明手持长矛来杀他,因此大受触动,反思和忏悔了
此前的罪恶人生。 提及搭救他的葡萄牙船长时,他说:“当我被葡萄牙船长从海上救起,
得到他公正、宽厚而仁慈的对待时,我思想中并没有丝毫的感恩之情。 当我再次遭遇海
难,差点在这岛边淹死时,我也毫无悔意,并未将之视为对我的惩罚。 我只是常常对自己
说,我是一条不幸的狗,生来就多灾多难。 ”(笛福,2018:96)
·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