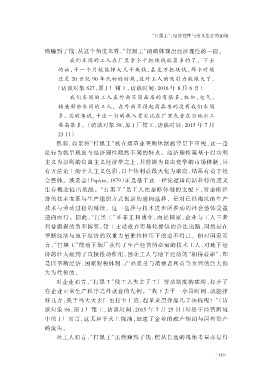Page 126 - 《社会》2021年第4期
P. 126
“打黑工”:经济理性与道义生存的困境
确赚到了钱,从这个角度来看,“打黑工”的确体现出经济理性的一面。
我们车间的工人在厂里拿个千把块钱就算多的了。 下去
的话,干一个月就能挣大几千块钱,甚至万把块钱,那个时候
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这对工人的吸引力就很大了。
(访谈对象 S27,原 J 厂钳工,访谈时间:2016 年 8 月 6 日)
我们车间的工人在外面买商品房的有很多,机加、电气、
铸造那些车间的工人, 在外面买得起商品房的没有我们车间
多。 总的来说,干这一行的收入肯定比在厂里或者在当地打工
要高很多。 (访谈对象 S8,原 J 厂钳工,访谈时间:2015 年 7 月
23 日)
然而,如果将“打黑工”放在烟草业垄断体制的背景下审视,这一违
法行为就呈现出与经济理性截然不同的特点。 经济理性奠基于以功利
主义为原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上,其前提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具
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色彩,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取向,结果有益于社
会整体。 波普金(Popkin,1979)正是基于这一理论逻辑向斯科特的道义
生存概念提出挑战。“打黑工”是工人在垄断体制的支配下,对垄断经
济的技术变革与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逆向选择, 是对已经淘汰的生产
技术与劳动过程的延续, 这一选择与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社会整体受益
逆向而行。 因此,“打黑工”并非正和博弈,而是国家、企业与工人三者
利益俱损的负和博弈。 钳工主动放弃市场化提供的合法出路,固然是在
垄断经济与地下经济的双重力量推拉挤压下的迫不得已, 但对国家而
言,“打黑工”使地下烟厂获得了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技术工人,对地下经
济的壮大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国企工人与地下经济的“相得益彰”,却
是以垄断经济、国家财税体制、产品质量与消费者利益等方面的巨大损
失为代价的。
对企业而言,“打黑工”使工人失去了工厂劳动制度的束缚,打开了
在企业正常生产秩序之外就业的先例。“我下去干一小段时间,就能挣
好几万,我干吗天天去厂里打卡上班,起早贪黑挣那几千块钱呢? ”(访
谈对象 S6,原 J 厂钳工,访谈时间:2015 年 7 月 25 日)对处于经营困境
中的 J 厂而言,这无异于火上烧油,加速了企业的破产倒闭与国有资产
的流失。
对工人而言,“打黑工”虽然赚到了钱,但从长远的视角考量亦是得
·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