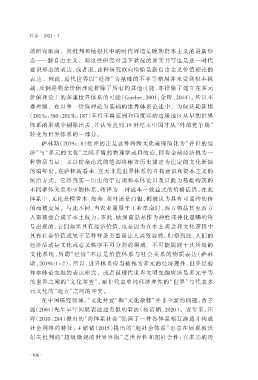Page 113 - 《社会》2021年第3期
P. 113
社会·2021·3
的研究取向, 其批判和植根其中的时代环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最新形
态———新自由主义, 而这些研究对当下状况的如实书写也是这一时代
意识形态的表达,或者说,这种研究取向恰恰是新自由主义价值理论的
表达。 因此,近代世界以“经济”为基础的不平等格局并未受到根本挑
战,反倒是剩余价值理论排除了所有的其他可能,亦排除了建立在多元
价值理论上的多重世界体系的可能( Graeber,2001;余昕,2014)。 所以不
难理解, 在以单一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论述中, 为何沃勒斯坦
(2013a:380;2013b:187)不得不将亚洲和印度洋的边缘地区从早期世界
体系的形成中剔除出去,并认为直到 19 世纪末中国才从“外部竞争场”
转变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萨林斯( 2019a:8)批评的正是这种将跨文化碰撞简化为“普世的经
济”与“多元的文化”之间矛盾的物理学或目的论,即将全球经济视为一
种物质力量, 又以宿命论式的笔调将地方历史描述为注定的文化渐蚀
的编年史。 在萨林斯看来,这无非是世界体系的自我意识和资本主义的
统治方式, 它将真实—历史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以及以此为基础构筑的
不同群体关系和事物体系,转译为一种成本—效益式的价格话语。 在此
体系中,无论是檀香木、海参、茶叶还是白银,都被认为具有可通约的价
值而被交易。 与此不同,当农业屈服于工业革命时,西方物品甚至西方
人都被整合成了本土权力。 在此,欧洲商品是作为神性或神化恩赐的符
号出现的,它们如果具有经济价值,也是因为在本土观念和文化逻辑中
具有社会价值或属于某种神圣类型而让人兴致盎然。 归根到底,人们的
经济活动是文化或意义秩序不可分割的领域, 不可能脱嵌于其所处的
文化系统,所谓“经济”不过是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物质表达(萨林
斯,2019b:1-2)。 所以,世界体系应当被视为多元的经济理性、世界经验
和本体论交融的表达形式, 或者说现代世界文明交融应该是多元平等
的世界之间的“文化并置”,而非代表单纯经济理性的“世界”与代表多
元文化的“地方”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研究领域,“文化并置”和“文化杂糅”并非全新的问题,费孝
通(2004)先生早年间就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杨清媚,2020)。 近年来,汪
晖 (2010:284)提出的“跨体系社会”强调了一种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
社会网络的特征;王铭铭(2015)提出的“超社会体系”也意在展现被沃
尔夫批判的“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之世界性和超社会性;在多元的历
·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