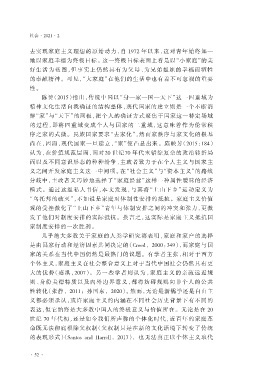Page 59 - 《社会》2021年第2期
P. 59
社会·2021·2
去实现家庭主义理想的原始动力,自 1972 年以来,这对青年始终如一
地以家庭幸福为终极目标。 这一终极目标表面上看是以“小家庭”的美
好生活为蓝图,但事实上仍然具有为父母、为兄弟姐妹的幸福而牺牲
的奉献精神。 可见,“大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性。
陈 赟 (2015)指出,传统中国以“身—家—国—天下”这一四重域为
精神文化生活自我确证的结构整体,现代国家的建立则是一个不断消
解“家”与“天下”的两极,把个人的确证方式聚焦于国家这一特定场域
的过程,即将四重域变成个人与国家的二重域,这意味着作为伦常秩
序之家的式微。 民族国家要求“去家化”,然而家秩序与家文化的根基
尚在,因而,现代国家一旦建立,“家”便凸显出来。 陈映芳( 2015:184)
认为,在价值规范层面,面对20 世纪70 年代末错综复杂的政治转折局
面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种种纷争,主政者致力于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
义之间开发家庭主义这一中间项。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路线
分歧中,主政者又巧妙地选择了“家庭经营”这样一种属性暧昧的经济
模式。 通过这组私人书信,本文发现,与其将“上山下乡”运动定义为
“ 乌托邦的破灭”,不如说是家庭对体制性安排的抵抗。 家庭主义价值
观的受挫激化了“上山下乡”青年与体制安排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更激
发了他们对制度安排的实际抵抗。 换言之,这实际是家庭主义抵抗国
家制度安排的一次胜利。
几乎绝大多数关于家庭的人类学研究都表明,家庭和家户的选择
是由国家行动和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Creed, 2000:349),而家庭与国
家的关系在当代中国仍然是最热门的议题。 有学者主张,相对于西方
个体主义,家庭主义在社会整合意义上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更
大的优势(盛洪,2007)。 另一些学者则认 为 ,家庭主义的亲 疏 远 近 规
则、身份美德特质以及内外边界意义,都将妨碍规则向非个人的公共
性转化(张静, 2011; 孙国东, 2020)。 然而,无论是新儒学还是自由主
义都必须承认,或许家庭主义的内涵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
表达,但它始终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终极意义与价值所在。 无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还是如今我们所声称的个体化时代,近百年的家庭革
命既无法彻底根除父权制(父权制只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转变了传统
的表现形式)(Santos and Harrell, 2017), 也无法真正以个体主义取代
·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