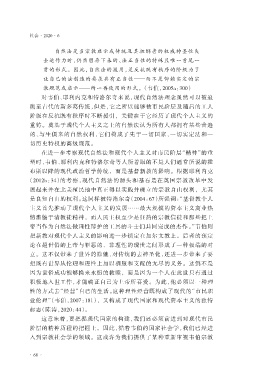Page 75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75
社会·2020·6
自然法是当宗教启示或传统及其担纲者的权威神圣性失
去运作力时,仍然留存下来的、法正当性的特殊且唯一首尾一
贯的形式。 因此,自然法的援用,是反抗既有秩序的阶级为了
让自己的法创造的要求具有正当性——而不是仰赖实定的宗
—
教规范或启示———所一再使用的形式。 (韦伯,2005a:300)
对韦伯、耶利内克和特洛尔奇来说,现代自然法理念虽然可以被追
溯至古代的斯多葛传统,但是,它之所以能够被市民阶层及随后的工人
阶级在反抗既有秩序时不断援引, 关键在于它经历了现代个人主义的
重铸。 奠基于现代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然法认为所有人都拥有某些普遍
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它们构成了先于一切国家、一切实定法和一
切历史特权的高级规范。
在进一步考察现代自然法和现代个人主义对市民阶层“精神”的重
塑时,韦伯、耶利内克和特洛尔奇等人所着眼的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霍
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传统, 而是基督新教的影响。 根据耶利内克
( 2012b:34)的考察,现代自然法的源头和基石是在英国宗教改革中发
展起来并在北美殖民地中真正得以实践并确立的宗教自由权利, 尤其
是良知自由的权利。这同样被特洛尔奇( 2004:67)所强调:“基督教个人
主义首先推动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业热
情滥觞于清教徒精神, 而人民主权至少是狂热的宗教信徒和那些把上
帝当作为自然法做理性辩护的工具的斗士们共同完成的杰作。 ”韦伯则
把新教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影响进一步锁定在加尔文教上。 后者的预定
论在超世俗的上帝与罪恶的、 非理性的现世之间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对
立。 这不仅带来了世界的除魅、对传统的去神圣化,还进一步带来了要
把既有世界从伦理和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的义务。 这倒不是
因为世俗成功能够换来永恒的救赎, 而是因为一个人在此世只有通过
积极地入世工作,才能确证自己为上帝所喜爱。 为此,他必须以一种理
性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生活。这种理性经营既构成了现代的“市民职
业伦理”(韦伯,2007:181), 又构成了现代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独特
标志(陈涛,2020:44)。
这意味着,要把握现代国家的构建,我们还必须前进到对现代市民
阶层的精神历程的把握上。 因此,循着韦伯的国家社会学,我们已经进
入到宗教社会学的领域。 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重新审视韦伯宗教
·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