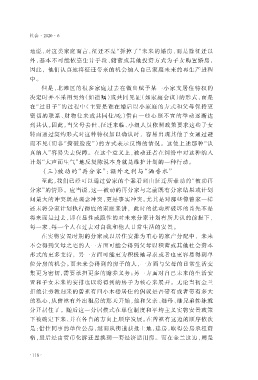Page 125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25
社会·2020·6
地说,对这类家庭而言,征迁不是“拆掉了”未来的婚房,而是除征迁以
外,基本不可能依靠生计手段、储蓄或其他投资方式为子女购置婚房,
因此, 他们认真地将征迁带来的机会纳入自己家庭未来的再生产进程
中。
但是,北滩区的很多家庭过去在做出赋予某一小家支居住特权的
决定时并不采用契约(如遗嘱)或共同见证(如家庭会议)的形式,而是
在“过日子”的过程中(主要是谁在婚后以小家庭的方式和父母保持更
密切的联系、财物往来或共同住/吃)借由一些心照不宣的举动逐渐达
到共认。因此,当父母去世、征迁来临、小组人员依照政策要求这些子女
转而通过契约形式对这种特权加以确认时, 容易出现其他子女通过避
而不见(而非“撕破脸皮”)的方式表示反悔的情况。 这使上述那种“认
真纳入”容易失去保障。 在这个意义上,被动迁者在纠纷中对这种纳入
计划“大声而生气”地反复陈说本身就是维护计划的一种行动。
(三)被动的“再分家”:额外之利与“洒香水”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曾家的个案看到由征迁所牵动的“被动再
分家”的情形。 应当说,这一被动的再分家与之前既有分家结果或计划
间最大的冲突既是观念冲突,更是事实冲突。 尤其是对那些像曾家一样
还未将分家计划执行彻底的家庭来讲, 此时的扰动所破坏的首先不是
将来而是过去,即在显性或隐性的对未来分家计划有所共认的前提下,
每一家、每一个人在过去对自我和他人日常生活的安置。
在实物安置时期的分家或以居住安排为重心的家产分配中, 未来
不会得到父母之宅的人一方面可能会得到父母以积蓄或其他社会资本
形式的更多支持, 另一方面可能更为积极地寻求或者也更容易得到单
位分房的机会。 而未来会得到的房子的人,一方面与父母的日常生活交
集更为密切,需要承担更多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安
置和子女未来的安排也以将得到的房子为核心来展开。 无论当初金兰
拒绝让劳教归来的曾褀有回小木楼居住的倡议是否带有或者带有多大
的私心,从曾褀有外出租房的那天开始,他和父亲、继母、继兄弟姊妹就
分开居住了。 随后这一分居模式在单位制度和平均主义实物安置政策
下被确定下来,并在各自的方向上顺序发展。 在曾褀有这边的顺序依次
是:借住同事的单位公房,继而从街道获批土地,建房,取得公房承租资
格,最后经由货币化拆迁置换到一套经济适用房。 而在金兰这边,则是
·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