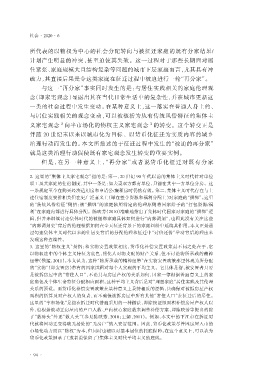Page 101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01
社会·2020·6
所代表的以物权为中心的社会分配转向与被征迁家庭的既有分家结果/
计划产生明显的冲突,甚至迫使其失效。 这一过程对于那些长期面对居
住紧张、家庭规模大且结构复杂等问题的城市下层家庭而言,尤其具有冲
破力,其直接后果是令这类家庭在征迁过程中被迫进行一轮“再分家”。
与这一“再分家”事实同时发生的是:与居住实践相关的家庭伦理观
念(即家宅观念)显露出其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并在城市更新这
一类的社会过程中发生变动。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落实在普通人身上的、
与居住实践相关的观念变动,可以被概括为从有传统风俗特征的集体主
2
3
义家宅观念 向半市场化的物权主义家宅观念 的转变。 这个转变正是
伴随 20 世纪末以来以城市化为目标、 以货币化征迁为实质内容的城乡
治理行动而发生的。 本文所描述的于征迁过程中发生的“被迫的再分家”
就是这类治理行动促使既有家宅观念发生转变的重要实例。
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再分家”或者说货币 化征迁对 既有分家
2. 这里的“集体主义家宅观念”指的是:第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集体主义时代针对单位
职工及其家庭的住宿制度,其中一条是:如夫妻双方都有单位,只能在其中一方单位分房。 这
一条规定至今在购买经济适用房和申请公/廉租房时仍然有效。 第二,集体主义时代存在与上
述住宿制度安排相关但在更广泛意义上(即在整个资源和福利分配上)对家庭的“捆绑”。这里
的“传统风俗特征”则指:被“捆绑”的家庭依照特定的伦理原则将国家给予的“打包资源/福
利”在家庭内部进行具体分配。 陈映芳(2010)准确地指出了集体时代国家对家庭的“捆绑”逻
辑,但并未继续讨论集体时代的被捆绑家庭具体如何进行“内部调剂”,也因此没有关注这些
“内部调剂史”背后的伦理根据如何在今天征迁背景下的家庭纠纷中延续其作用。本文正是通
过勾连集体主义时代以来的住居史背后的分配伦理和征迁中“讨价还价”举动背后的理由来
发现这种连续性。
3. 这里的“物权主义”是指:和实物安置政策相比,货币化补偿安置政策最不同之处在于,它
以物权法中的个体主义特征为底色,强化人对物支配的财产关系,但不讨论物所承载的精神
纽带(侯猛,2011)。本文认为,这种“物所承载的精神纽带”在实物安置政策那里体现为所分配
的“实物”(即安置房)带有的国家试图对每个人实现的平均主义。 它具体是指,被安置者只要
是被拆房屋中的“常住人口”,不论其与房屋产权的关系如何,国家一律根据普遍意义上的家
庭角色及个体生命特征分配相应面积。这种平均主义背后是对“理想家庭”居住实践及其伦理
关系的预设。 而货币化补偿安置政策在某种意义上秉持相反的逻辑,只确保对被拆房屋产权
面积的折算及对产权人的负责,而不确保被拆房屋中所有其他“常住人口”在征迁后的居住。
这里的“半市场化”是指在拆迁时代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即除按证照面积补偿房屋产权人以
外,也根据被动迁房屋内的户口人数、户内核心家庭数来调整补偿方案,即陈映芳等提出的除
了“数砖头”外还“数人头”(参见陈映芳,2010;王娜,2011)。 例如,本文中的下江市在拆迁时
代就将因动迁变得确无居处的“无房户”纳入安置范围。 因此,货币化政策尽管因房屋入市的
市场化动力而以“物权”为本,但同时也辅以对基本居住的托底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
货币化政策继承了(或者说保留了)集体主义时代平均主义的底线。
·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