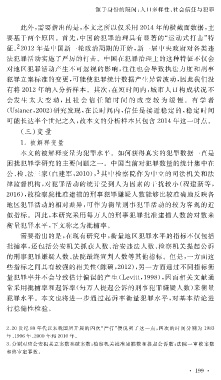Page 206 - 《社会》2020年第4期
P. 206
源于身份的隔阂 : 人口多样性 、 社会信任与犯罪
此外 , 需要指出的是 , 本文之所以仅采用 2014 年的横截面数据 , 主
要基于两个原因 。 首先 , 中国的犯罪治理具有显著的 “ 运动式打击 ” 特
征 。 2 年是中国新一轮政治周期的开始 , 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各类违
2012
法犯罪活动实施了严厉的打击 。 中国在犯罪治理上的这种特征不仅会
对地区犯罪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往往也会导致执法力度和刑事
犯罪立案标准的变更 , 可能使犯罪统计数据产生异常波动 , 因此我们没
有将 2012 年纳入分析样本 。 其次 , 在短时间内 , 城市人口构成状况不
会发生太大变动 , 且社会信任随时间的改变较为缓慢 。 有学者
( 犝狊犾犪狀犲狉 , 2002 ) 研究发现 , 在长时间内 , 信任是接近稳定的 , 稳定时间
可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 故本文的分析样本只包含 2014 年这一时点 。
( 三 )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犯罪水平 。 如何获得真实的犯罪数据一直是
困扰犯罪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 中国当前对犯罪数量的统计集中在
公 、 检 、 法三家 ( 白建军 , 2010 ), 3 其中检察院作为中立的司法机关和法
律监督机构 , 对犯罪活动的统计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较小 ( 程建新等 ,
2016 ), 故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各
地区犯罪活动的相对差异 , 可作为衡量刑事犯罪活动的较为客观的近
似指标 。 因此 , 本研究采用每万人的刑事犯罪批准逮捕人数的对数来
衡量犯罪水平 , 下文称之为批捕率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现有研究中 , 衡量地区犯罪水平的指标不仅包括
批捕率 , 还包括公安机关抓获人数 、 治安违法人数 、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数 、 法院最终宣判人数等其他指标 。 但是 , 一方面这
些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 陈硕 , 2012 ), 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指标衡
量犯罪率并不会导致估计偏误的产生 ( 犔犲狏犻狋狋 , 1998 ), 因而相关文献通
常采用批捕率和起诉率 ( 每万人提起公诉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数 ) 来衡量
犯罪水平 。 本文也将进一步通过起诉率衡量犯罪水平 , 对基本结论进
行稳健性检验 。
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所开展的四次 “ 严打 ” 便说明了这一点 , 四次的时间分别为 1983
年 、 1996 年 、 2000 年和 2010 年 。
3. 分别对应公安机关立案数和破案数 ;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数和提起公诉数 ; 法院一审收案数
和终审定罪数 。
9
1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