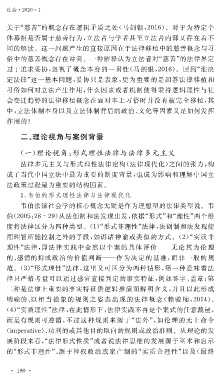Page 197 - 《社会》2020年第1期
P. 197
社会 · 2020 · 1
关于 “ 慈善 ” 的概念存在逻辑矛盾之处 ( 马剑银 , 2016 )。 对于为特定个
体募捐是否属于慈善行为 , 立法者与学者甚至立法者内部又存在着不
同的解读 。 这一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法律移植中的慈善概念与习
俗中的慈善概念存在冲突 。 一种解释认为立法者对 “ 慈善 ” 的法律界定
过于追求妥协 , 忽视了概念本身的一贯性 ( 马剑银 , 2016 )。 回到 “ 谁决
定法律 ” 这一基本问题 , 妥协只是表象 , 更为重要的是回答法律移植和
习俗如何对立法产生作用 , 什么因素或者机制使得秉持逻辑理性与社
会变迁趋势的法律移植概念在面对本土习俗时并没有被完全移植 , 其
中 , 立法体制本身以及立法体制背后的政治 、 文化等因素又是如何发挥
作用的?
二 、 理论视角与案例背景
( 一 ) 理论视角 : 形式理性法律与法律多元主义
法律多元主义与形式理性法律建构 ( 法律现代化 ) 之间的张力 , 构
成了当代中国立法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背景 , 也成为影响和理解中国立
法政策过程最为重要的结构因素 。
1. 韦伯的形式理性法律与法律现代化
韦伯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无疑是作为理想型的法律类型说 。 韦
伯 ( 2005 : 28-29 ) 从法创制和法发现出发 , 依据 “ 形式 ” 和 “ 理性 ” 两个维
度将法律区分为四种类型 。( 1 )“ 形式非理性 ” 法律 , 法创制和法发现使
用理智所能控制之外的手段 , 如诉诸神谕或类似的方式 。( 2 )“ 实质非
理性 ” 法律 , 即法律实践中全然以个案的具体评价 ——— 无论其为伦理
的 、 感情的抑或政治的价值判断 ——— 作为决定的基准 , 而非一般的规
范 。( 3 )“ 形式理性 ” 法律 , 这里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形 , 第一种意味着法
律只严格考量可以通过感官直接判定的事实特征 , 例如签字 、 盖章 ; 第
二种是法律上重要的事实特征借逻辑推演而解明含义 , 并且以此形成
明确的 、 以相当抽象的规则之姿态出现的法律概念 ( 赖骏楠 , 2014 )。
( 4 )“ 实质理性 ” 法律 , 在此情形下 , 法律实践不再是个案式的任意裁量 ,
而是有规则可遵循 , 不过这种规则来源于 “ 法外 ”, 如伦理的无上命令
( 犻犿 狆 犲狉犪狋犻狏犲 )、 功利的或其他目的取向的规则或政治准则 。 从理论的发
展阶段来看 ,“ 法律形式性质 ” 或者说法律思维的发展源于巫术和启示
的 “ 形式非理性 ”、 源于神权政治或家产制的 “ 实质合理性 ” 以及 ( 最终
0
· 9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