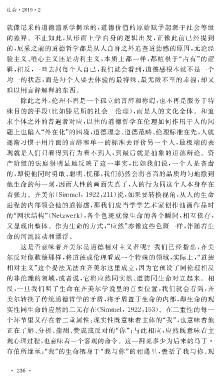Page 243 - 201902
P. 243
社会· 2019 · 2
就像尼采的道德谱系学揭示的,道德价值的原始赋予起源于社会等级
的差异。不止如此,从形而上学自身的逻辑出发,正像此前已经提到
的,尼采之前的道德哲学都是从人自身之外追查道德感的原因,无论经
验主义、唯心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本质上都一样,都植根于“占有”的逻
辑,相反,一旦去问每个人自己,我们就会看到,道德感根本就不是一个
均一的状态,而是每个人要去体验的最特殊、最无微不至的幸福,却又
难以用言辞解释的东西。
除此之外,伦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言辞和称谓,也不再是服务于特
殊目的的手段(比如滕尼斯的社会—伦理),而是人的文化全体。和追
求个体之外的普遍者对应,以往的道德哲学在伦理如何作用于人的问
题上也陷入“外在化”的困境,道德理念、道德范畴、伦理标准在先,人就
逐渐习惯于用片面的言辞和单一的标准去评价另一个人,最极端的表
现就是人们只看得到行为看不到人,到最后就是抽象的道德辩论。资
产阶级的法庭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事实,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是吝啬
的,即使他同时勇敢、聪明、忧郁,我们仍然会将吝啬的品质均匀地撒到
他生命的每一刻,因而人性的画面失真了,人的行为同这个人本身存在
着张力。齐美尔( 犛犻犿犿犲犾 , 1922 : 211 )说,如果要转换视角,从人的生命
进程的内部领会他的道德感,那我们应当学学艺术家创作油画作品时
的“网状结构”( 犖犲狋狕狑犲狉犽 ),各个色斑就像生命的各个瞬间,相互依存,
又显现出整体。作为生命的方式,“应然”亦像这些色斑一样,伴随着生
命的河流波动和漂浮。
这是否意味着齐美尔是道德相对主义者呢?我们已经指出,齐美
尔反对像歌德那样,将道德或伦理看成一个特殊的领域,实际上,“道德
相对主义”这个提法无法在齐美尔这里成立,因为它预设了同伦理相反
的非伦理的领域,或者说,它将应然同实然、道德同生命对立起来。相
反,一旦我们明了生命在齐美尔学说里的首要位置,我们就会看到,齐
美尔转换了传统道德哲学的矛盾,将矛盾置于生命的内部,即生命的现
实性同生命的应然的二元存在( 犛犻犿犿犲犾 , 1922 : 153 )。在二重性的每一
个环节里又存在着二重属性:现实性既意味着主体的“我”,也意味着他
正在了解、分析、揣测、赞成或反对的“你”;与此相应,应然既意味着主
观心理过程,也意味着一个客观的命令。这一洞见多少为后来的马丁·
布伯所继承:“我”的生命栖身于“我与你”的相遇里,囊括了我与你、现
· 2 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