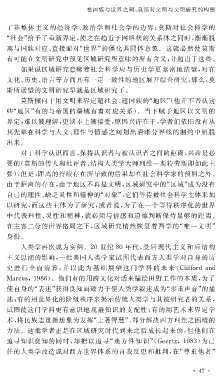Page 54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54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了非整体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边界;莫斯对社会科学的
“社会”给予了重新界定,使之在趋近于网络状的关系体之同时,渐渐脱
离与国族对应、直接面对“世界”的僵化共同体意象。这就必然使莫斯
有可能在文明研究中预见区域研究所意味的所有含义,并超出于这些。
如果说区域研究意味着社会科学应与历史学更紧密地结盟,对在
文化、历史、语言等方面具有一定一致性的地区展开综合研究,那么,莫
斯所展望的文明研究早就是区域研究了。
莫斯倾向于用文明来界定超社会、超国族的“地区”(他并不否认这
些“地区”有的与帝国的疆域有着对应关系)。当下赋予地区以文明的
界定,难以被理解,更谈不上被接受,原因兴许在于,学者们依旧没有从
其先辈在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情感之间划出清晰分界线的制约中解脱
出来。
对于科学认识而言,保持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距离,兴许是必
要的(莫斯的传人和批评者、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即如此主
张),但是,距离的持续存在所导致的后果却在社会科学家的预料之外。
由于距离的存在,由于地区不再是文明,区域研究中的“区域”成为没有
自己的理性、缺乏灵性和精神的“对象”,它们等待被社会科学主体来加
以研究,而这些主体为了研究,或者说,为了在一个等待秩序化的世界
中代表理性、灵性和精神,就必须与情感和道德判断保持足够的距离。
在主客二分的世界格局之下,区域研究悄然恢复着西学的“唯一文明”
身份。
人类学再次成为实例。 20 世纪 80 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
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试图代表西方人类学对自身的历
史进 行 全 面 清 算,并 以 此 为 基 础 展 望 这 门 学 科 的 未 来 ( 犆犾犻犳犳狅狉犱犪狀犱
犕犪狉犮狌狊 , 1986 )。他们有的用跨文化对话来描绘田野工作的本质,为了
使自身的“表述”获得良知而致力于使人类学叙述成为“多重声音”的描
述;有的用世界化的阶级秩序来揭示传统人类学与其被研究者的关系,
试图使这门学科更有意识地规避知识的支配性;有的用艺术来界定学
术,将民族志重新想象为发挥“土著智慧”、部分解决西方理性之困境的
方法。这批学者正是在区域研究时代到来之后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在
追寻知识良知的同时,却把以追寻“地方性知识”( 犌犲犲狉狋狕 , 1983 )为己
任的人类学改造成对西方世界体系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在“尊重他者”
· 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