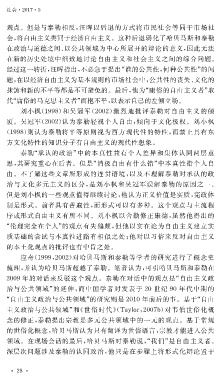Page 35 - 《社会》2017年第5期
P. 35
社会· 2017 · 5
观点。但是与泰勒相反,汪晖以后退的方式将市民社会等同于市场社
会,将自由主义类同于经济自由主义。这种后退弱化了哈贝马斯和泰勒
在政治与道德之间、以公共领域为中心所展开的辩论的意义,因此无法
在新的历史处境中细致地讨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综合问题。
经过这一转折,汪晖指出,不必急于提出“谁的公共性,何种公共性”的问
题,在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本规则的市场社会中,公共性的丧失、文化的
抹煞和新的不平等都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他为“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取
代“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抱不平,以表示自己的左倾立场。
刘小枫( 1998 )和吴冠军( 2002 )激烈地批评泰勒对自由主义的颠
覆。吴冠军( 2002 )认为泰勒轻视个人自由,倾向于文化极权。刘小枫
( 1998 )则认为泰勒将平等原则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而禁止具有东
方文化特性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想象。
泰勒“承认的政治”中的本真性兼有个人差异和集体认同两层意
思,其研究重心在后者。但是“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中本真性指个人自
由。不了解这些文章所形成的连贯语境,以及不理解泰勒对承认的政
治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区分,是刘小枫和吴冠军误解泰勒的原因之一。
但是刘小枫的一些观点值得继续讨论,他认为正义价值是实质,宪政体
制是形式。前者具有普遍性,而形式可以有多种。这个观点与主流程
序或形式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刘小枫以舍勒修正康德,虽然他得出的
“伦理完全在个人”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以实在论为自由主义建立实
质基础的尝试与本真性进路有相似之处;他对以习俗来反对自由主义
的本土化观点的批评也有中肯之处。
应奇( 1999 , 2002 )对哈贝马斯和泰勒等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概念史
梳理,并认为哈贝马斯超越了泰勒。笔者认为,可引哈贝马斯和泰勒在
2009 年的对话来反驳这个观点。泰勒在对话中的观点是“自由主义政
治与公共领域”的延伸,而中国学者对发表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的研究则是 2010 年前后的事。基于“自由
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和《世俗时代》( 犜犪 狔 犾狅狉 , 2007犫 )对韦伯世俗化概
念的修正,泰勒提出宗教是多元公共领域中的一元的观点。基于常规
的世俗化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翻译为世俗语言,宗教才能进入公共
领域。在现场会话的最后,哈贝马斯对泰勒说,“我们”是自由主义者。
深层次问题涉及泰勒的认同政治,他只是在步骤上将形式化辩论置于
· 2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