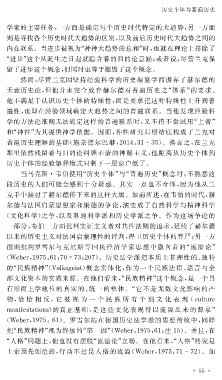Page 62 - 《社会》2017年第1期
P. 62
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
学家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确定每个历史时代特定的大趋势,另一方面
则是寻找各个历史时代大趋势的区别,以及前后历史时代大趋势之间的
内在联系。当进步被视为“种种大趋势的总和”时,也就在理论上排除了
“进步”这个从诞生之日起就隐含着的目的论意涵;或者说,尽管兰克保
留了进步这个概念,但同时也等于摧毁了这个概念。
然而,尽管兰克因坚持经验科学的历史编纂学而摒弃了赫尔德的
天意历史论,但他并未完全放弃赫尔德对普遍历史之“体系”的要求。
他不满足于认识历史个体的特殊性,而是要求把这种特殊性上升到普
遍性,也即在经验领域确定大趋势之间的普遍联系。当他发现经验科
学的方法论准则无法确定这样的普遍联系时,又不得不尝试用“上帝”
和“神性”为其提供神学依据。因而,神性研究归根结底构成了兰克对
普遍历史理解的基础(施奈德尔巴赫, 2014 : 31-35 )。换言之,在兰克
那里依然残留着与目的论纠缠不清的神秘主义,他距离从历史个体到
历史个体的经验解释模式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
当马克斯·韦伯使用“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概念时,不熟悉这
段历史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十分疑惑。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从兰
克手中接过了赫尔德传下来的这杆大旗。如前所述,在韦伯的时代,赫
尔德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康德的争论,演变成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
(文化科学)之争,以及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之争。作为这场争论的
一部分,韦伯一方面批判实证主义者对共性法则的追求,延续了赫尔德
以来的历史主义对法国启蒙理性的评判,捍卫历史个体的尊严;另一方
面则批判罗雪尔与克尼斯等国民经济学家思想中隐含着的“流溢论”
( 犠犲犫犲狉 , 1975 : 61 ; 70-73 ; 207 )。历史法学派把本质上非理性的、独特
的“民族精神”( 犞狅犾犽狊 犵 犲犻狊狋 )概念实体化,作为一个民族法律、语言与全
部文化资本的实质来源。在他们看来,“民族精神”这个概念,是一个具
有形而上学地位的真实的、统一的整体。“它不是无数文化影响的产
物,恰 恰 相 反,它 被 视 为 一 个 民 族 所 有 个 别 文 化 表 现 ( 犮狌犾狋狌狉犲
犿犪狀犻犳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的真正 基 础,是 这 些 文 化 表 现 得 以 流 溢 出 来 的 源 泉”
( 犠犲犫犲狉 , 1975 : 61 )。罗雪尔站在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思想传统中,同样
把“民族精神”视为终极的“第一因”( 犠犲犫犲狉 , 1975 : 61 ;注 15 )。并且,在
“人格”问题上,他也没有摆脱“流溢论”立场。在他看来,“人格”终究是
上帝预先创造的,行动不过是人格的流溢( 犠犲犫犲狉 , 1975 : 71-72 )。如
· 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