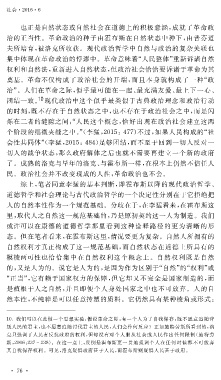Page 83 - 《社会》2016年第6期
P. 83
社会· 2016 · 6
也正是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在道德上的积极意涵,成就了革命政
治的正当性。革命政治的种子由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中种下,由普芬道
夫所培育,被洛克所收获。现代政治哲学中自然与政治的复杂关联也
集中体现在革命政治的悖谬中。革命意味着“人民整体”重新诉诸自然
权利和自然法,重新进入自然状态,但政治社会恰恰要诉诸于革命为其
奠基。革命不仅构成了政治社会的开端,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政
治”。人们在革命之际,似乎最可能在一起、最充满友爱、最上下一心、
团结一致。 10 现代政治中这个似乎最类似于古典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动
的时刻,既不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也不存在于政治社会之中,而是闪
烁在二者的缝隙之间:“人民这个概念,恰好出现在政治社会建立这两
个阶段的细微夹缝之中。”(李猛, 2015 : 477 )不过,如果人民构成的“社
会性共同体”(李猛, 2015 : 484 )足够团结,而不至于回到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状态,那么政府解体之后也就不需要再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了。成熟的洛克与早年的洛克、与霍布斯一样,在根本上仍然不信任人
民。政治社会并不改变现成的人性,革命政治也不会。
综上,笔者同意李猛的基本判断,即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
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与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决定性分别在于它拒绝把
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一个规范基础。分歧在于,在李猛看来,在霍布斯这
里,取代人之自然这一规范基础的,乃是原初契约这一人为制造。我们
或许可以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那里看到这种诠释路径的更为清晰的形
态。但在笔者看来,在霍布斯这里,情况要更为复杂。自然人所拥有的
自然权利才真正构成了这一规范基础,而自然状态在道德上所具有的
模棱两可性也恰恰集中在自然权利这个概念上。自然权利既是自然
的,又是人为的。说它是人为的,是因为作为区别于“自然”的“权利”或
“正当”,它有赖于国家权力的保障,但它却又不完全是国家制造的,而
是植根于人之自然,并且即便个人身处国家之中也不可放弃。人的自
然本性,不纯粹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它仍然具有某种棱角或形式:
10. 我们可以在此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革命之际,有一个人为了自我保存,既不愿意追随背
叛人民的君主,也不愿意追随讨伐君主的人民,人们会作何反应?正如施特劳斯所看到的,洛
克只强调了人民有反抗政府的权利,但却没有对个人服从社会或人民作出任何限制(施特劳
斯, 2006 : 237-238 )。在这一点上,反倒是霍布斯更一贯地强调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放弃
其自我保存权利。可见,洛克疑惧政府甚于人民,而霍布斯则疑惧人民甚于政府。
· 7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