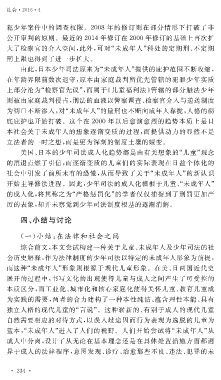Page 241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241
社会· 2016 · 4
犯少年案件中的调查权限。 2008 年的修订则在部分情形下打破了非
公开审判的原则。最近的 2014 年修订在 2000 年修订的基础上再次扩
大了检察官的介入空间,此外,可对“未成年人”科处的定期刑、不定期
刑上限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由此,日本少年司法原来为“未成年人”提供的庇护范围不断收缩,
在年龄界限前数次退守,原本由家庭裁判所优先管辖的犯罪少年实质
上部分沦为“检察官先议”,而属于《儿童福利法》管辖的部分触法少年
则被由家庭裁判侵占,刑法的血液以警察调查、检察官介入与逆送制度
为切口不断渗入,对“未成年人”的量刑也不断向成年人靠拢,人格的彻
底庇护也开始打破。这个在 2000 年以后愈演愈烈的趋势本质上是日
本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的想象逐渐变质的过程,而提供动力的显然不是
立法者的一时之想,而是更为深刻的制度土壤的嬗变。
美国、日本的少年司法成人化趋势都是由有关想象的“儿童”观念
的消退点燃了引信,而逐渐变质的儿童们的实际表现在日益个体化的
社会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从而导致了关于“未成年人”的新认识
开始主导修法进程。因此,少年司法的成人化植根于儿童、“未成年人”
的成人化,将其称之为“严格惩罚化”的学者仅仅捕捉到了刑罚更加严
厉的表象,却并未察觉到少年司法制度根基的逐渐消解。
四、小结与讨论
(一)小结:在法律和社会之间
综合前文,本文尝试构建一种关于儿童、未成年人及少年司法的社
会历史解释,作为法律制度的少年司法以特定的未成年人形象为前提,
而这种“未成年人”形象则根源于现代儿童形象。在美、日两国近代史
展开的过程中,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可受控的
本质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使得关怀儿童、教育儿童成
为实践的需要,两者的合力建构了一种本性纯洁、蕴含理性本能、具有
独立人格的现代儿童的“言说”。这种崭新的、有别于成人的现代儿童
自然需要相应的对待方式,以误入歧途因而行为表现为逸脱的儿童为
蓝本,“未成年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尝试将“未成年人”从
成人中分离,设计了从无论在基本理念还是在具体处置措施方面都迥
异于成人的法律程序,意图发现、诊疗、治愈那些不良、违法、犯罪的未
·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