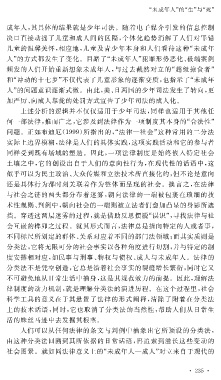Page 242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242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
成年人,其具体的结果就是少年司法。随着电子媒介引发的信息控制
决口直接动摇了儿童和成人间的区隔,个体化趋势消解了人们对罪错
儿童的温馨关怀,相应地,儿童及青少年本身和人们看待这种“未成年
人”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目睹了“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恶化、极端案例
频发的人们开始重新想象未成年人,与过去截然对立的“超级掠食者”
和“冲动的十七岁”不仅代表了儿童形象的逐渐变质,也指示了“未成年
人”的问题意识逐渐式微。由此,美、日两国的少年司法发生了转向,更
加严厉、向成人靠拢的处罚方式宣告了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上述分析的逻辑并不仅仅适用于少年司法,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任
何一部法律,推而广之,它涉及到法律作为一项制度其本身的“合法性”
问题。正如布迪厄( 1999 )所指出的,“法律—社会”这种常用的二分法
实际上边界模糊,法律是人们的具体实践,这项实践活动和它的参与者
同样受到既有场域的塑造。因此,一项法律制度是始终嵌入特定社会
土壤之中,它的创设出自于人们的意向性行为,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这
似乎可以为民主政治、大众传媒和立法技术所直接化约,但不论是意向
还是具体行为都时刻关联着作为整体而呈现的社会。换言之,在法律
与社会之链的两头都分布着迷雾,朝向法律的一端被包裹在琐细的技
术性规则、判例中,朝向社会的一端则被立法者们愈加凸显的身影所遮
挡。穿透这两层迷雾的过程,就是借助反思摆脱“误识”,寻找法律与社
会互嵌的榫卯之过程。就其形式而言,法律总是指向特定的人或者事,
不同标尺所划定的群体、关系对应着不同的部门法领域;而其实质则是
分类法,它将无限可分的社会事实以各种角度进行切割,并与特定的制
度安排相对应,如民事与刑事、物权与债权、成人与未成年人。法律的
分类法不是凭空创造,它总是沿着社会事实的裂缝增长繁衍,同时它又
不可避免地从日常生活中抽身,这是其规范效力的前提。因此,理解法
律制度的动力机制,就是理解分类法的演进历程。在这个过程里,社会
科学工具的意义在于其悬置了法律的形式阐释,清除了附着在分类法
上的技术话语,同时,它也取消了分类法的当然性,帮助人们从日常生
活的蛛丝马迹中去发掘其根茎。
人们可以从任何法律的条文与判例中抽象出它所预设的分类法,
由这种分类法回溯到其所依据的日常话语,再追索到滋长这些变动的
社会图景。就如同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成人”对立来自于现代的
· 2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