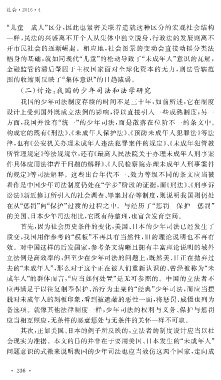Page 243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243
社会· 2016 · 4
“儿童—成人”区分,因此也紧密关联着造就这种区分的宏观社会结构
一样,民法的兴盛离不开个人从集体中独立脱身,行政法的发展则离不
开市民社会的逐渐崛起。相应地,社会图景的变动会直接动摇分类法
栖身的基础,就如同现代“儿童”的松动导致了“未成年人”意识的瓦解,
金融监管的滞后肇因于主权国家面对全球化资本的无力,刑法管辖范
围的收缩则反映了“集体意识”的日趋减弱。
(二)讨论:我国的少年司法和法学研究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存续的时间不足三十年,如前所述,它在制度
设计上受到国外既成立法例的影响,得以直接引入一些成熟制度;另一
方面,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少年司法,而是散落在位阶不一的条文中。
构成它的既有《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
律,也有《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未成年犯管教
所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的规定》等司法解释。这些出台年代不一、效力等级不同的条文应当被
看作是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仍处在“学步”阶段的证据,而《刑法》、《刑事诉
讼法》新近修订所引入的社会调查、罪案封存等制度,则说明我国则仍处
在从“惩罚”向“保护”过渡的过程之中。与经历了“惩罚—保护—惩罚”
的美国、日本少年司法相比,它既有待整理,也富含发育空间。
首先,因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美国、日本的少年司法已经发生了
质变,我国用作参考的“模板”不再具有当然性,旧的理论说明也不再有
效。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参考条文清晰且拥有丰富理论说明的域外
立法例是高效率的,但至少在少年司法的问题上,既然美、日正在抛弃过
去的“未成年人”,那么对于这个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的、曾经被称为“未
成年人”的群体而言,“应当如何处置”是无可参照的。中国的立法者不
应再满足于以往复制奉保护、治疗为圭臬的“经典”少年司法,而应当摆
脱对未成年人的刻板印象,看到被遮蔽的恶性一面,将惩罚、威慑也列为
备选项。就像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少年司法的权利与义务、保护与惩罚
应当相互照应,无条件的恶意惩处与无条件的关怀一样不可取。
其次,正如美国、日本的例子所反映的,立法者的制度设计应当以社
会现实为准据。本文的目的并非在于要用美国、日本发生的“未成年人”
问题意识的式微来说明我国的少年司法也应当效仿这两个国家,走向成
· 2 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