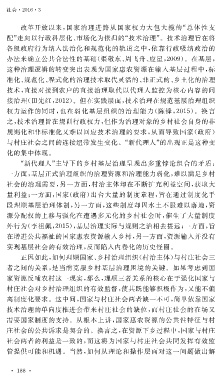Page 195 - 《社会》2016年第3期
P. 195
社会· 2016 · 3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进路从国家权力大包大揽的“总体性支
配”走向以行政科层化、市场化为依归的“技术治理”。技术治理旨在将
各级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之中,依靠行政吸纳政治的
办法来确立公共合法性的基础(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2009 )。在基层,
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突出表现为国家惠农资源在输入基层过程中,标
准化、规范化、程式化的治理技术取代灵活的、非正式的、乡土化的治理
技术,直接对接到农户的直接治理取代以代理人监控为核心内容的间
接治理(田先红, 2012 )。但在实践层面,技术治理在规范基层治理组织
权力运作的同时,也在弱化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陈锋, 2015 )。换言
之,技术治理旨在规训行政权力,但作为治理对象的乡村社会自身的非
规则化和非标准化又难以回应技术治理的要求,从而导致国家(政府)
与村庄社会之间的连接纽带发生变化。“新代理人”的出现正是这种变
化的集中体现。
“ 新代理人”主导下的乡村基层治理呈现出多重悖论组合的矛盾:
一方面,基层正式治理组织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弱化,难以满足乡村
社会的治理需要,另一方面,村治主体却在不断扩充利益空间,获取大
量利益;一方面,国家(政府)出台大量的制度章程,旨在通过制度化手
段理顺基层治理体制,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却因水土不服难以落地,资
源分配权的上移与强化在遭遇多元化的乡村社会时,催生了大量制度
外行为(李祖佩, 2015 ),基层治理实际与规则之治相去甚远;一方面,旨
在增进公共福祉的国家惠农资源输入乡村,另一方面,资源输入并没有
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反而陷入内卷化的历史怪圈。
正因如此,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三
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克服乡村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如果考虑到国
家资源反哺农村这一现实,那么,理顺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强化国家与
村庄社会对乡村治理组织的有效监督,使其既能够积极作为,又能不偏
离制度化要求。这中间,国家与村庄社会两者缺一不可,简单依靠国家
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推进会带来村庄社会的缺位,而村庄社会的在场又
需要国家制度的支持。从根本上讲,国家惠农资源的公共性特征与村
庄社会的公共诉求是契合的。换言之,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国家与村庄
社会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将为国家与村庄社会共同发挥有效监
管提供可能和机遇。当然,如何从理论和操作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
· 1 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