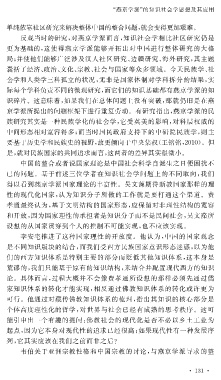Page 138 - 《社会》2015年第4期
P. 138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单纯依靠社区研究来解决整体中国的整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反观当时的研究,对燕京学派而言,知识社会学相比社区研究仍是
更为基础的,这使得燕京学派能够开拓出对中国进行整体研究的大格
局;并使他们能够广泛涉及汉人社区研究、边疆研究、海外研究,其主题
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与国家等众多领域。今天民族学、社
会学和人类学三科孤立的状况,无非是国家体制对学科拆分的结果,实
际每个学科负责不同的微观研究,而它们的知识基础都有燕京学派的知
识碎片。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总体问题上没有突破,那就仍旧是在燕
京学派所提出的问题框架下进行重复劳动。有研究指出,燕京学派的民
族研究其实是一种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它受英美的影响,对科层权威的
中间形态相对宽容得多;而当时国民政府支持下的中研院民族学,则主
要基于历史学和民族史的视野,故更倾向于中央集权(王铭铭, 2010 )。但
是,就对民族国家的共同追求而言,这两者的差异其实很微小。
中国的整合或者说国家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自诞生之日便困扰不
已的问题。基于前述三位学者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上的不同取向,我们
得以看到燕京学派国家理论的丰富性。吴文藻期待新教国家那样的理
性的现代化国家,认为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费
孝通最终认为,基于文明结构的国家形态,应保留对非理性结构的宽容
和开放,因为国家理性的承担者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民间社会,吴文藻所
设想的从国家贯穿到个人的控制不可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
李安宅推进了这种国家理性的开放度。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观念
是不同知识版块的结合,而我们受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迷惑,以为他
们的西方知识体系是特别主要的部分而贬低其他知识体系,这本身是
荒谬的,我们只能基于原有的知识结构,来结合并配置现代西方的知识
论。具体而言,过程大概并不会像费孝通所设想的那样必须先通过儒
家知识体系的转化才能实现,相反通过佛教知识体系的转化或许更为
可行。他通过对藏传佛教知识体系的梳理,指出其知识的核心部分是
个体高度理性化的哲学,对世界与社会已经有成熟的思考秩序。这可
能引申出一个有趣的提问:佛教社会的现代化是否不必以乡土工业为
起点,因为它本身对现代性的追求已经很高;如果现代性有一种发展序
列,它其实应该在我们之前而非之后?
韦伯关于亚洲宗教性格和中国宗教的讨论,与燕京学派寻求的整
· 1 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