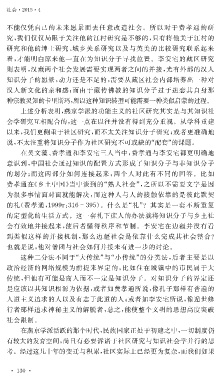Page 137 - 《社会》2015年第4期
P. 137
社会· 2015 · 4
不能仅凭自己的未来愿景而去任意改造社会。所以对于费孝通的研
究,我们仅仅局限于关注他的江村研究是不够的,只有将他关于江村的
研究和他的绅士研究、城乡关系研究以及与英美的比较研究联系起来
看,才能明白原来他一直在为知识分子寻找位置。李安宅的藏区研究
则表明,汉藏两个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并接,光有外部的汉人
知识分子的愿景,动力还是不足的,需要从藏区社会内部培养出一种对
汉人新文化的亲和感;而由于藏传佛教的知识分子过于迷恋其自身那
种宗教灵知的卡里斯玛,所以这种知识转型可能需要一种类似启蒙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燕京学派的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其实是与其知识社
会学研究互相配合的,这一点在以往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从学科重建
以来,我们更侧重于社区研究,而不太关注知识分子研究;或者更准确地
说,不太注重将知识分子作为社区研究不可或缺的“配套”的课题。
在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三人当中,费孝通与李安宅都更明确地
意识到,中国社会通过知识的配置方式形成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
的划分;而这两部分如何连接起来,两个人对此有不同的回答。比如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当中谈到的“熟人社会”,之所以不需要文字是因
为很多事情面对面就能解决,而这种人与人的接触依靠的是彼此默契
的礼(费孝通, 1999狉 : 316-395 )。什么是“礼”?其实是一套不断重复
的定型化的生活方式。这一套礼下庶人的办法就将知识分子与乡土社
会有效地并接起来,使后者懂得秩序和节制。李安宅在边疆并没有看
到类似这样的并接机制,那么边疆社会是依靠什么完成其社会整合?
也就是说,他对僧团与社会如何并接未有进一步的讨论。
这种二分法不同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类法,后者主要是以
政治经济的网络规模为前提来界定的,比如住在城镇中的市民属于大
传统,但他有可能是商人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界定还
是应该以其知识根源为依据,或者如费孝通所说,像孔子那样有普遍的
人道主义追求的人以及有志于此道的人;或者如李安宅所说,像遁世修
行者那样追求神秘主义的解脱者,总之,能使整个文明的思想高度突破
社会限制。
在燕京学派活跃的那个时代,民族国家正处于初建之中,一切制度仍
有较大的发育空间,尚且有必要诉诸于社区研究与知识社会学并行的思
考。经过这几十年的变迁与积累,社区实际上已经更为复杂,而我们如果
· 1 3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