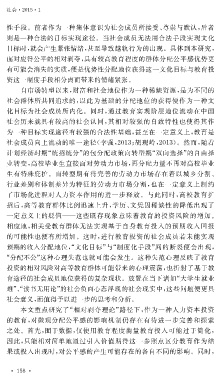Page 165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165
社会· 2015 · 1
性手段。前者作为一种集体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尊崇与默认,后者
则是一种合法的目标实现途径。当社会成员无法用合法手段实现文化
目标时,就会产生紧张情绪,甚至导致越轨行为的出现。具体到本研究,
面对应得公平的相对剥夺,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群体分配公平感优势更
有可能会消失的实质,便是优势性分配地位获得这一文化目标与教育投
资这一制度手段相分离而带来的情绪紧张。
自市场转型以来,财富和社会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为不同的
社会群体所共同追求的,以此为基础的分配地位的获得便作为一种文
化目标为社会成员所内化。同时,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地位流动在中国
社会历来就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其相对较强的自致特性也使得其作
为一种目标实现途径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
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李强, 2013 ;胡现岭, 2013 )。然而,随着
计划经济时期“统招统分”的包分配政策向转型期“双向选择”的自由择
业转变,高校毕业生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再分配力量不再对高校毕业
生有特殊庇护。而转型期有待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以城乡分割、
行业差别和体制差异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在一定意义上制约
了市场化进程对人力资本作用的进一步释放。与此同时,高校教育扩
招后,高等教育群体比例迅速上升,学历、文凭因稀缺性的降低出现了
一定意义上的贬值———这些既存现象意味着教育的投资风险的增加。
相应地,相关受教育群体无法实现基于自身教育投入的预期收入回报
的可能性也便有所增加。这时,进行教育投资的社会成员若未能实现
预期的收入分配地位,“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间的断裂便会出现,
“ 分配不公”这种心理失范也就可能会发生。这种失范心理反映了教育
投资的相对风险对高等教育群体可能带来的心理震荡,也折射了基于教
育途径的社会成员地位获得的复杂现状。放置在当下诸如“大学生就业
难”、“读书无用论”的社会负面心态浮现的社会现实中,这些问题便更具
社会意义,而值得予以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了“相对剥夺理论”路径下,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的教育,对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仍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之处。首先,囿于数据,仅使用教育程度衡量教育投入可能过于简化,
因此,只能相对简单地通过引入价值期待这一参照点区分教育作为结
果或投入出现时,对公平感的产生可能存在的各自不同的影响。同时,
· 1 5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