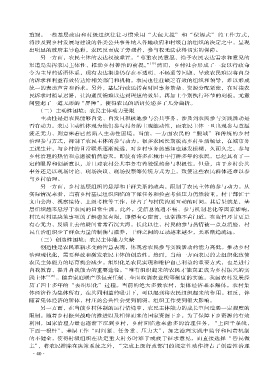Page 42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P. 42
重视。一些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往往习惯采用 “大包大揽”和 “保姆式”的工作方式,
将涉及到乡村发展与建设的各类公共事务纳入各地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的决定之中,呈现
出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农民反而成了旁观者,参与权无法获得切实的保障。
另一方面,农民主体的表达权被虚置。“尊重农民意愿、给予农民表达需求和意见的
渠道是发挥农民主体性、推动乡村善治的前提。” 然而,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套以行政命
〔 19〕
令为主导的话语体系,现有表达渠道仍存在不透明、不畅通等问题,导致农民难以将自身
的诉求和利益有效传达给相关部门和机构。农民也往往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难以形成
统一的表达声音和诉求。另外,基层行政运转有时因事务繁杂、资源分配紧张,在对接农
民诉求时稍显迟滞,让沟通反馈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再加上个别执行环节的刻板,无意
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 “屏障”,使得农民的话语传递多了几分曲折。
(二)主动性困境:农民主体动力受限
主动性是指农民能够自觉、自发且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涉及到农民参与实践活动是
否有动力。农民主动性体现为他们参与村务的主观能动性,而农民主体一旦出现参与意愿
疲乏无力,则意味着已然陷入主动性困境。当前,一方面农民的 “脱域”和传统的乡村
治理参与方式,抑制了农民主体的参与动力。很多农民长期脱离乡村生活场景,在城市务
工谋生计,与乡村的日常联系逐渐疏远,对乡村事务的感知也越发模糊,久而久之,参与
乡村治理的热情和意愿被悄然磨灭。即使有许多在城市中打拼多年的农民,已经具有了一
定的眼界和创新意识,并且对农村公共事务有着较强的参与积极性。但是,由于乡村公共
事务还是以现场讨论、现场决议、现场投票等传统方式为主,致使这些农民群体还难以参
与乡村治理。
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组织的悬浮和干群关系的疏离,限制了农民主体的参与动力。从
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乡村基层组织面临的下派任务和检查考核压力仍然较重。村干部忙于
文山会海、视察接待、上级考核等工作,挤占了与村民沟通互动的时间。其后果就是,基
层组织越来悬浮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受信息流通不畅、参与机制老化等因素影响,
村民对村里决策事项的了解愈发有限,即便有心建言,也常摸不着门道。在监督环节更是
有心无力,反馈上去的疑问常常石沉大海。长此以往,村民的参与热情被一点点消磨,村
民自治组织少了群众力量的制衡与滋养,干群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关系渐趋疏远。
(三)创造性困境:农民主体能力欠缺
创造性是农民革新求变的智慧表现,体现着农民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高低。推动乡村
治理现代化,需要释放和激发农民主体的创造性。然而,当前一方面农民的去组织化致使
农民主体能力的培育机会减少。组织化是农民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重要方式,也是进行
自我教育、提升自我能力的重要途径。“唯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实
践主体”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取消农业税等制度的实施,我国农村发展经
〔 20〕
历了四十多年的 “去组织化”过程。当前的绝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基本解体。农村集
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在共同利益的吸引下,可以起到将农民组织起来的作用。相反,伴
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村庄的公共性会受到削弱,组织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另一方面,在当前乡村体制的运行情境中,农民主体能力的成长空间遭遇一定程度的
限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以及相伴而来的国家资源下乡,为了保障下乡资源的有效
利用,国家治理力量也逐渐下沉到乡村,乡村面临愈来愈多的治理任务,“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加之治理实践中监督和问责机制
的不健全,使得村级组织在决定重大村务时难于或疲于征求意见,而直接选择 “替民做
主”,将农民排除在决策系统之外,“完成上级行政部门的规定性动作挤占了创造性治理
0 ·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