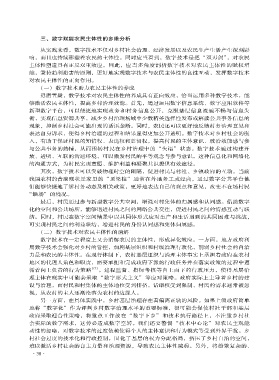Page 40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P. 40
三、数字赋能农民主体性的多维分析
从实践来看,数字技术不仅对乡村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
响,而且也持续形塑着农民的主体性。同时应当看到,数字技术是把 “双刃剑”,对农民
主体性塑造具有正反双重效应。因此,应当多角度剖析数字技术对农民主体性的赋权增
能,秉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更好地实现数字技术与农民主体性的良性互动,发挥数字技术
对农民主体性的正向作用。
(一)数字技术助力农民主体性的养成
毋庸置疑,数字技术对农民主体性的养成具有正向效应,恰当运用多种数字技术,能
够激活农民主体性,提高乡村治理效能。首先,通过运用数字信息系统、数字应用软件等
新型数字平台,可以便捷地实现政务和村务信息公开,克服基层信息流通不畅与信息失
衡,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减少乡村治理场域中少数精英选择性发布或解读公共事务信息的
现象,抑制乡村社会可能出现的话语垄断。同时,农民还可以更好地反馈村务治理意见和
表达自身诉求,使得乡村治理的过程和结果显得更加公开透明。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的嵌
入,有助于保证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村民的主体意识、政治效能感与参
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从而扭转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 “失语”状态。数字技术通过构建开
放、透明、互联的沟通环境,可以激发村民的平等观念与参与意识。这种信息化和网络化
的沟通方式,为村民实现意愿、维护利益和凝聚共识提供有效途径。
其次,数字技术可以突破物理时空的阻隔,促进村民与村社、乡镇政府的互动。当前
我国农村的普遍现状是家里的 “顶梁柱”通常在外地务工或经商,通过数字公共平台他
们能够快捷地了解村务动态及相关政策,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改变不在场村民
“缺场”的境况。
最后,村民通过参与新型数字公共空间,增强对村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借助数字
化的空间和公共场所,能够增进村民之间的网络公共交往,促进村民之间的情感互动与联
结。同时,村民在数字空间情景中以共同体形式应对生产和生活遇到的共同困难与挑战,
可实现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增进村民的身份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
(二)数字技术对农民主体性的消解
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消解农民的主体性,形成异化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利
用数字技术会强化对乡村的管控,加剧基层组织和村级治理行政化,削弱乡村社会的自治
力量和农民的主体性。在现行体制下,农村基层组织与治理主体事实上承担着政府在农村
地区的代理人角色和职责,需要承担和完成政府下派的行政任务并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遵
循着向上负责的行为策略 。过程监督、指标考核等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使得基层治
〔 17〕
理主体在现实中可能会采取 “数字形式主义”等应对策略。政府实际上主导着乡村的建
设与治理,而村民和村集体的主体地位受到排挤,话语权受到限制,村民的需求通常被忽
视,从农村的主人逐渐沦落为农村的边缘人。
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中,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着偏离正轨的风险。如果上级政府简单
地将 “数字化”作为评判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很可能会促使村社干部和基层
政府采取迎合性策略,将重点工作放在 “数字下乡”和技术执行路径上,不注重乡村社
会实际的数字需求,这势必造成数字空转。我们还要警惕 “技术中心论”对农民主观能
动性的忽略,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使得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行为模式等受到外界干扰。乡
村社会过度的技术化和行政控制,固化了基层的权力分配格局,挤压了乡村自治的空间,
难以激活乡村社会的自主力量和治理资源,导致农民主体性减弱。另外,将纷繁复杂的、
8 ·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