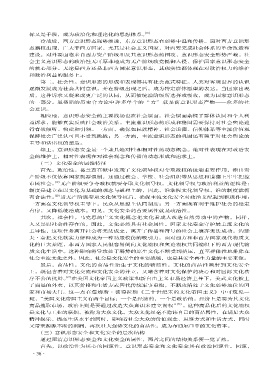Page 38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P. 38
标又是手段,成为政治化和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 18〕
冷战后,西方意识形态强势渗透,东方意识形态在弱势中温和传播。面对西方意识形
态霸权出现,广大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内要完成社会体系的革命改造和
建设,对外要面临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和反共意识形态的围攻,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严峻。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无可厚非地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抵御入侵、保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的核心部分。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其现实性都体现在对政治权力的维护
和政治利益的服务上。
第二,社会性。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表现都具有社会范式特征。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共同意识,并在阶级出现之后,成为特定群体愿望的表达。当国家出现
后,这种诉求又凝聚成更广泛的认同,从而被统治阶级所选择或吸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的一部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中许多单个的 “力”就是前意识形态产物———众多的社
会意识。
相应地,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战场也在社会层面。社会层面杂糅了群体认同和个人利
益诉求,能够真实反映社会政治关系。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稳固需要保持对社会舆论进
行有效倾听、构建和引领。一方面,确保如民族精神、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等主流价值观
保持社会广泛认可且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还有赖于对社会舆论的
主导和话语权的塑造。
综上,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兼具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动态概念。绝对性表现在对政治安
全的维护上,相对性表现在对社会观念和传播的动态形成和追求上。
(二)文化安全的属性特征
首先,政治性。葛兰西在狱中发现了文化领导权对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作用,指出资
产阶级不仅依靠国家机器强制,还通过教会、学校、社会组织等从思想和道德上牢牢把控
市民社会。 无产阶级要争夺政权就要夺取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与政治利益的逻辑是:
〔 19〕
制度是建立在以文化为基础的观念与道理上的,因此,谁掌握文化领导权,谁的制度就拥
有合法性。 当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后,确保主流文化安全对政治支配起到积极作用:
〔 20〕
一方面在文化领导权主导下,民众从思想上认同制度;另一方面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有序,又降低统治成本。可见,文化安全的首要属性就是政治性。
其次,社会性。马克思的广义文化概念把文化看成人改造自然劳动中的产物。同样,
人又是以社会性存在的,因此,文化必然具有社会属性。国家文化安全守护最主流文化的
主导性,这项任务离开社会将无法成立,离开了传播和符号的社会土壤亦无法成功。约瑟
夫·奈把文化软实力解释成为一种劝服模仿的吸引力。面对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现代物质文
化的巨大差距,非西方国家人民很容易倒向文化霸权和舆论霸权共同编织下的西方现代物
质文化生活中。这种影响将导致处于弱势的原生文化不断受到挤压,直至群体性地排除在
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因此,社会是文化安全的主要战场,也是其安全再生力量的主要来源。
最后,商品性。文化的商品性衍生于文化的物质性。文化的商品性映射到文化安全
上,既包含着对文化交流和文化安全的并立,又暗含着对文化保护的决心和对国际文化秩
序不公的抗辩。 在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主导下,美式文化披上
〔 21〕
了商品的外衣,以其价格和生活方式替代传统军事重炮,不断攻陷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国
家和市场大门。这一点在詹姆斯·彼得拉斯 《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中可窥见一
斑,“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
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 。这种商品化后的文化霸权
〔 22〕
是文化与工业的联姻,被称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丝毫不隐讳自己的商品属性,在满足大众
精神娱乐、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影响着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
又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再次壮大强势文化的商品性,成为布迪厄口中的文化资本。
(三)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层次结构
通过厘清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属性,两者之间的结构关系便一览了然。
首先,以政治性为核心的同源性。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具有政治同源性。同源,
6 ·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