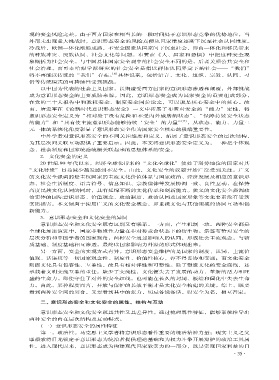Page 37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P. 37
现的安全风险之差。由于西方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意识形态竞争的优势地位,当
外部未出现重大挑战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点便从国家维度逐渐下沉至社会认同维度。
冷战后,欧洲一体化渐趋成熟,不安全因素从国家间下沉至社会,即由一体化和移民带来
的种族冲突、民族认同、社会文化等问题。布赞在 《人、国家和恐惧》中把这种安全现
象概括为社会安全。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社会安全不同的是,后者关照公共安全和
社会治理,而哥本哈根学派研究的社会安全是指以群体认同界定下的社会——— “我们”
将不再能以传统的 “我们”存在。 具体说来,包括语言、文化、组织、宗教、认同、习
〔 16〕
俗等传统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外部挑战
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和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同位论之,可以说是核心安全中的核心。故
而,唐爱军在 《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一文中拓展了布赞对安全的 “能力”定性,将
意识形态安全定义为 “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保障持续安全状态
的能力”和 “具有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持续 ‘安全’的力量” ,从状态、能力、力量三
〔 17〕
元一体的系统化角度彰显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核心的极端重要性。
中外学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不同关注维度和定义,拓展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层次结构,
为其层次间关联互动提供了重要启示。因此,本文将意识形态安全定义为,一种把个体观
念、社会制度和国家统治统摄关联起来的思想体系的安全。
2. 文化安全的定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文化全球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对其
“文化特质”日益减少越发感到不安全。由此,文化安全的议题开始广泛受到关注。广义
的文化安全强调的是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及相应的意识形
态、社会生活制度、语言符号、信息知识、宗教信仰等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在保持
高度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具有延绵不断的文化传承和创新能力。狭义的文化安全强调政
治实体的国际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认同及国家形象等文化要素没有受到
实质损害。本文倾向于使用广义的文化安全概念,即重视文化与其他领域的协同互动和创
新能力。
3. 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异同
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产生机制一致。两种安全都是
全球化加速演进中,国家非物质性力量在非对称竞合状态下的衍生物。借鉴布赞对安全的
层次分析和中国学者的国家视角,两种安全通过影响人的认同,形成社会主流观念,与物
质基础、制度基础相互渗透,最终以国家影响力外溢的形式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安全的实现方式有异。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是国家的制度、认同、主流价
值观、话语权等一切国家观念性、制度性、价值性核心,容不得妥协和变通;而文化安全
则因文化具有包容性、互鉴性,故具有相对弹性和可塑性。除了塑造文化的安全底线,还
承载着文明交流互鉴的重任。缺少了交流性,文化便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革新的活力和旺
盛的生命力。即使守住了对外的安全红线,也可能在长久的封闭、板结和僵化中失去生命
力。由此,某种程度而言,开放与保护的长效平衡才是文化安全构建的关键。综上,既要
看到两种安全间的契合,又要看到其中的张力,切忌各说各话,以安全为名,相互否定。
二、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属性、结构与互动
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既具共性又具差异性。通过梳理属性特征,能够系统推导出
两种安全的内在层次结构及互动模式。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属性特征
第一,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意识形态看作重要的统治精神力量;现实主义之父
摩根索将目光锁定于意识形态为统治者提供理论基础和为权力斗争开展辩护的政治工具属
性。进入现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构建现代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既是实现国家利益的目
5 ·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