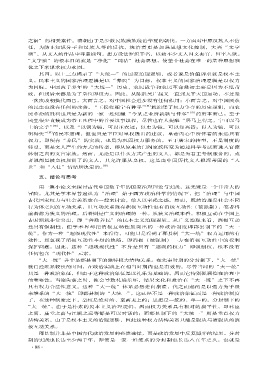Page 90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90
之祸”的相关案件。清朝由于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华夏的朝代,一方面对中原汉族人不信
任,为防止知识分子和汉族人等的反抗,统治者更是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 “文字
狱”,从文人的作品中寻章摘句,想方设法罗织罪名,以致不少文人因文去官、因字入狱。
“文字狱”的根本目的就是 “净化”“纯洁”社会思想,使整个社会在唯一的某种思想驯
化之下来谋求权力永固。
其四,以上三点揭示了 “大统一”的国家治理逻辑,或者说是价值诉求就是权本主
义。民本主义的国家治理逻辑是以 “养民”为目标,权本主义的国家治理逻辑是以权力
为目标。中国两千多年的 “大统一”历史,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最初主要是因为不堪苛
政,但到后来都是为了皇位即权力。因此,从陈胜吴广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
一次次改朝换代而已,大而言之,对中国社会进步没有任何作用;小而言之,对中国民众
的民生也没有任何的改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就演绎了权力争夺的历史逻辑,而农
〔 86〕
民革命的胜利也只是为新的一家一姓炫耀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的资本而已。至于
〔 87〕
民生很少直接成为帝王日程中的首要议事议程,尽管也有人提醒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
上治之乎” ,以及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 88〕
明得失” 的民本道理,但也只是下臣对皇权提出的建议,皇帝内心中所怀着的永远只有
〔 89〕
权力,即便有 “养民”的实践,也是为巩固权力服务的。至于唐宋的转型,不是制度的
转型,而是文人产生的方式的转型,即从原来的门阀家族转变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僚
体制之内的文官家族。然而,无论是以什么方式产生的文人,都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或
者说都是被皇权规训了的文人,只允许服从皇权。这是由中国历代文人根深蒂固的 “入
世”和 “入仕”情结所决定的。
〔 90〕
五、结论与思考
用一篇小论文来探讨古代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
冒险。尤其是学术界普遍认为 “治理”始于西方政治科学的情况下,把 “治理”与中国
古代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放在一起来讨论,给人以牵强之感。然而,既然治理是社会不同
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互动关系既有积极互动性也有消极互动性 (被强制),笔者将
前者称为狭义的治理,后者则是广义的治理的一种。从狭义治理来看,积极互动在中国上
古时期就非常突出,即 “善政养民”的民本主义治理逻辑。从广义治理来看,消极互动
性具有强制性,但学术界却把消极互动性最突出的一种政治制度即郡县制下的 “大一
统”,作为一种 “超级现代性”来看待,可能只是看到了郡县制 “大一统”权力运用的有
效性,却忽视了消极互动性本身的缺陷,即消极 (被强制)一方在消极互动性中的权利
保护问题。因此,这种 “超级现代性”本身是只有 “超级的权力”即强制权,根本没有
任何包含 “现代性”元素。
“大一统”并非是郡县制下的独特权力结构关系。在先秦时期的分封制下,“大一统”
就已经维系较长的时间,在政治实践上在相当时期内也是有效的。尽管当时的 “大一统”
只是一种政治象征,但由于这种政治象征是以礼乐为基础的,因而它特别强调德在治理中
的重要性。当德失落之时,便会导致礼崩乐坏,结果文化和政治在 “大一统”之下不再
具有权力合法性意义。这种 “大一统”体系必然走向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以强力为手段
来维系的 “大一统”即郡县制的 “大统一”。这已经不是一种政治象征而是一种政治制度
了,在这种制度之下,皇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思想是一统的、单一的。分封制下的
“大一统”,由于是朴素的民本主义治理逻辑,因而权力关系具有相对的扁平性,即君臣
之间、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等都是可以对话的;而郡县制下的 “大统一”则是垂直权力
结构关系,由于是权本主义的治理逻辑,因此这种权力结构关系只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消
极互动关系。
郡县制并非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是政治发展中反复博弈的结果。分封
制的实践也长达至少两千年,即便是一家一姓维系的分封制也长达八百年之久。也就是
8 ·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