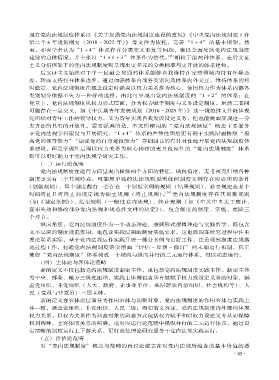Page 47 - 《党政研究》2022年第2期
P. 47
现有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 《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第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 2018 - 2022 年)》等文件为依托,完善 “ 1 + 4”的基本框架。然
而,亦有学者认为 “ 1 + 4”体系存在分类交叉重复等问题,难以全面反映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的总体情况,并主张以 “ 1 + 1 + 3”体系作为替代。 相较于前两种体系,在后实证
〔 38〕
主义分析框架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则呈现出更多元的分类标准与更开放的体系建构。
后实证主义始终对于单一且融会贯通的体系能够自我维持在完整领域内持有怀疑态
度,转而支持打开体系边界,通过加强体系内部各类别间及体系内外交互,维持体系的相
对稳定。党内法规制度在概念设定时强调以权力关系作为核心,使用权力作为体系内部各
类别划分依据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由此可呈现出党内法规制度的 “ 1 + 2”的体系:在
党章下,党内法规制度从权力形式层面,分为权力赋予制度与义务设定制度。虽然二者间
可能存在一定交叉,如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 2016 - 2025 年)》这一规范性文件既体现
党组织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权力,又为青年实现自我发展设定义务,但也能侧面展现这一分
类方法所具有的开放性。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 “党内法规制度”概念主要服务
于党内法规学科建设与开展研究,“ 1 + 4”体系的严整性固然更有利于实践层面按照 “提
高党的领导能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能力”等创制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建设,但是学理性层面以权力关系为核心构建的更具包容性的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则可以更好助力于党内法规学研究工作。
(三)运行论范畴
党内法规制度在运行方面呈现出横纵两个方面的特征。横向角度,麦考密克归纳各种
制度事实有三个共同特点:可能用单独的法律规则说明任何制度实例存在所必须的条件
(创制规则)、每个制度都有一套存在一个制度实例的规则 (结果规则)、必要规定在某个
时间终止且将终止的规定视为独立规则 (终止规则)。 党内法规制度存在其创制规则
〔 39〕
(如 《制定条例》)、结果规则 (一般性党内法规)、终止规则 (如 《中共中央关于废止、
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包含制度的制定、实施、废除三
个环节。
纵向角度,党内法规制度作为一个动态理论,兼顾形式逻辑理论与实践哲学,既包含
文本层面的制度规范作用,也包含实践层面的制度实施要求。这也强调在研究过程中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基于党内法规运作实践开展一部分案例与田野工作,注重观察制度法规落
地过程工作,打通党内法规制度落实层面 “评估 -反馈 -修订”的末端运行机制,真正
使得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成一个横向与纵向并行的二元运行体系,得以动态运行。
(四)主体论与客体论范畴
新的定义不仅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制定主体,也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实践主体。制定主体
为中央、部委、地方三级党组织,实践主体则包含所有被赋予权力或设定义务的对象,涵
盖党组织、非党组织 (人大、政府、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机构等)、人
民 (党员与非党员)三层主体。
新的定义在客体论层面分为作用客体与调整对象,党内法规制度的作用客体与实践主
体一致,涵盖党组织、非党组织、人民三级;而如前文所述,党内法规制度内外部均体现
权力关系,以权力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调整方式包括权力赋予和以权力设定义务从而保障
权利两种。主客体间关系的明确,也对应运行论范畴中横纵并行的二元运行体系,通过设
定清晰的制度运行上下游关系,更好地使理论研究服务于党内法规实践运行。
(五)价值论范畴
对 “党内法规制度”概念与范畴的再讨论建立在对党内法规所蕴含的基本价值的遵
5 ·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