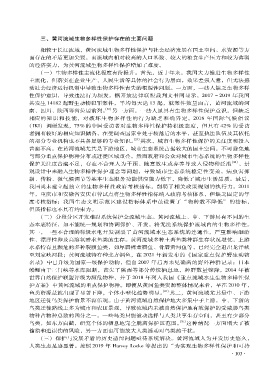Page 105 - 《党政研究》2022年第2期
P. 105
三、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较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在国土空间、水资源等方
面存在的矛盾更加尖锐,而流域内相对较高的人口基数、较大的粮食生产压力和较为薄弱
的经济实力,为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了难度。
(一)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程度有待提升。首先,近十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但落实在企业生产、人民生活等具体的社会行为层面,效果差强人意,但无法撼
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中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源性问题。一方面,一些人缺乏生物多样
性保护意识,导致违法行为频发。据开放法律联盟裁判文书网显示,2017 - 2019 年我国
共发生 14182 起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平均每天达 13 起,就案件数量而言,黄河流域的河
南、四川、陕西等省位居前列。 另一方面,一些人虽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但缺乏
〔 22〕
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缺乏准确界定。2018 年国际气候倡议
( IKI)调研发现,75%的中国受访者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积极态度,但只有 42%的受访
者拥有较好的相应知识储备,在受调查国家中处于较落后的水平,甚至执法队伍及其依托
的部分专业机构也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 其次,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度和投入
〔 23〕
普遍不高。在黄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城市生态系统占据较大的国土空间,不可避免地
与部分重点保护物种分布或迁徙区域重叠。然而政府和公众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关注度普遍不足,存在不合理人为干预、随意放生或弃养导致入侵物种泛滥 、景
〔 24〕
观设计中未融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等问题,导致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变差,病虫害抑
制、传粉、微气候调节等基本生态服务功能供应能力低下,降低了城市生活品质。最后,
我国尚未建立起独立的生物多样性政府考核指标,削弱了相关政策规划的执行力。2011
年,重庆市和安徽省安庆市曾试点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但缺乏固定的年
度考核指标;我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中虽设置了 “物种数不降低”的指标,
但该指标也不具有约束力。
(二)分段分区开发难以系统保护全流域生态。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具有不同的生
态本底特征,如不能统一规划和协调保护、开发,将无法系统保护流域内的生物多样性。
其一,一些不合理的梯级水电开发割裂了黄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严重影响洄游
性、漂浮性卵及高溶氧需求鱼类的生存。黄河流域多种土著鱼类种群生存状况堪忧,上游
水系特有且濒危的多种裂腹鱼类,如厚唇裸重唇鱼、骨唇黄河鱼等,已经完全退出龙洋峡
至刘家峡河段;黄河流域特有种北方铜鱼,在 2021 年新发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中已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自 2007 年后再未见确凿的野外种群记录;日本
鳗鲡由于三门峡等水库阻断,丧失了陕西等部分传统栖息地,种群数量骤降,2014 年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级为濒危物种,并于 2018 年列入我国 《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案》中黄河流域的重点保护物种。即便从黄河鱼类资源整体情况来看,早在 2010 年,
鱼类资源量就出现了显著下降,个体小型化趋势明显。 其二,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
〔 25〕
地区迁徙鸟类保护前景不容乐观。由于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地大多集中于上游,中、下游的
鸟类迁徙路线上多为城市和农田景观,导致流域内未被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的受威胁鸟类
物种占物种总数的四分之一。一些鸟类只能被动选择与人类共享生存空间,甚至有少部分
鸟类,如东方白鹳,研究个体的栖息地完全脱离保护区范围。 这种情况一方面增大了被
〔 26〕
偷猎和遭误伤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放大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干扰。
(三)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历史遗留问题亟待系统解决。黄河流域人为开发历史悠久,
人类生态足迹显著。按照 2019 年 Harvey Locke 等提出的 “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
0 · ·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