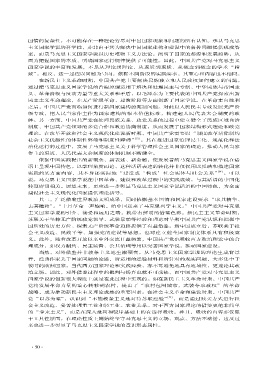Page 51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P. 51
国情的复杂性,不可能存在一种理论穷尽对中国国家现象和问题的所有认知。承认马克思
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亦非由于其为解决中国国家建构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
案,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从
而为把握国家的本质、明确国家运行规律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从概念到概念的学术 “精
致”。相反,这一过程以问题为导向,依据不同阶段的实践要求,其重心和内容也不相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政权如何建立的问题。
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普遍原理运用于解决和处理民主与专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
义、革命阶级与反动力量等重大关系和矛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过渡阶段等方面创新了国家学说。在革命走向胜利
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进行新国家建构的宪制问题。对此以人民民主专政发展无产阶
级专政,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建构的根本价值标准,构建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政党关系的过程中建立健全了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发展了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和政党
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需要以 “制度改革清除制约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制性弊端和制度性障碍” 。其在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规范化和法
〔 33〕
治化运行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推动人民当家
作主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依据中国实践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述、新命题,使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话
语上呈现中国特色。以学理角度而论,这种话语表述的转化并非仅仅用以反映和描述国家
实践的某方面内容,其本身还实际地 “建造或 ‘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可以
〔 34〕
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实践成效,与其话语的中国化
转型密切相关。展望未来,更应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话语的中国特色,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指导。
其三,广泛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同时依据基本国情和国家建设要求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
主义国家学说的引介、接受和运用之端,就带有鲜明的借鉴色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苏联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武装暴动等经验和理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中
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关于社
会主义改造、民族平等、加强党的建设等思想,也对建立健全国家制度体系具有积极意
义。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共产党也吸收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合
理成分,如权力制约、民主监督、公共治理等用以完善国家学说,推动国家建设。
当然,对外借鉴并非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生成背景
看,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所运用的经验材料和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大多集中于
彼时的欧洲国家。当代西方国家理论和实践经验,亦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性,更遑论其政
治立场。因此,对外借鉴过程中的批判与扬弃也就不可或缺,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此过程中实现的。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将发展革命力量的重心转移到农村,提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战略,成为推动新民主主义理论成熟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
党 “以苏为鉴”,认识到 “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苏联经验” ,而是通过赎买方式进行社
〔 35〕
会主义改造、妥善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对于西方国家理论的借鉴更绝非简单
的 “拿来主义”,而是在深入批判和驳斥基础上的有选择吸收。并且,吸收的内容亦仅限
于工具性层面,在理论性质上则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动摇,这反过
来也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属性。
0 ·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