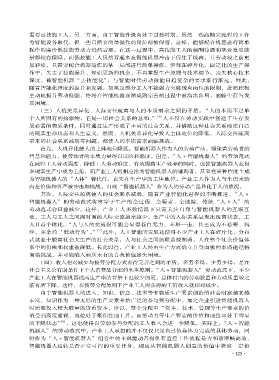Page 12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
P. 126
需要高技能工人,另一方面,由于智能升级尚处于过渡时期,虽然一些高精尖流程的工作
为智能设备取代,但一些只需要简单操作的岗位却被保留,这样,能够配合机器进行简单
操作的廉价低技能劳动力仍然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高技能工人的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前
景都较有保障,而低技能工人虽然看起来在智能机器冲击下保住了饭碗,且劳动较之前更
加轻松,只需要配合机器运作的某一局部进行简单操作,但却在碎片化、固定化的生产操
作中,失去了技能提升、知识更新的机会,不再掌握生产原理与技术细节,丧失核心技术
深度,被智能机器 “去技能化”,与智能时代劳动技能日趋复杂的要求渐行渐远。因此,
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和发展,如果这部分工人不能强力突破现有岗位的限制,进而积极
主动地提升劳动技能,终将在智能机器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面临生存与发
展困境。
(三)人机关系异化、人际交往疏离与人的本质需求之间的矛盾。“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不仅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生存发
〔 6〕
展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时通过生产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并借助这种社会关系确定自己
的现实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然而,人机关系异化导致人主体地位的降低、人际交往疏离
带来的社会联系减弱等问题,都使人的本质需求面临挑战。
首先,人机异化使人的主体地位降低。智能机器人作为人的劳动产品,凝聚着劳动者的
智慧和能力,使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得以反映和确证。但是,“人 +智能机器人”的劳动范式
在减轻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劳动难度、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智能机器人在很
多现实生产中成为主角,而产业工人则相应沦为智能机器人的辅助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智能机器人的 “人体”替代件,丧失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产业工人作为人与生俱来的
内在价值和尊严被冲击和挑战,出现 “智能机器人”作为人的劳动产品异化于人的状况。
其次,人际交往疏离使人的社会联系减弱。随着产业智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 +
智能机器人”的劳动范式将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全要素、全链接,传统 “人 +人”的
劳动范式会日益减少。这样,产业工人多数情况下只需关注自身与智能机器人的互联互
动,工人与工人之间面对面的人际交流越来越少,生产中的人际关系呈现出疏离状态,工
人日益个体化。“人与人的交流很可能会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甚至成为不必要、羁
绊、多余的 ‘低效行为’。” 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还使得不少产业工人在碎片化、分布
〔 7〕
式就业中脱离社会大生产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人在整个社会价值体
系中的份额和权重被降低。长此以往,产业工人经由生产方式确立自身面貌的本质途径将
面临挑战,并可能陷入前所未有的自我价值迷失困境。
(四)收入相对减少与按劳分配方式有待完善之间的矛盾。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是在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人 +智能机器人”劳动范式下,不少
产业工人在智能机器提高生产率的背景下也较少加班,总体付出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较之
前有所下降,这样,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产业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就相对减少。
由于智能机器人的进入,知识、信息、技术等非物质生产要素创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
丰富,知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开始广泛的参与到分配中,加之企业引进智能机器人
时需要投入较大数量的货币资本,所以,整个分配中 “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价
值受到高度重视、地位处于聚积性地上升,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值和地位却处于明显
的下降状态” ,这也使得以劳动参与分配的工人收入会进一步降低。实际上,“人 +智能
〔 8〕
机器人”的劳动范式中,产业工人承担的并不仅仅只是自己依靠体力完成的具体劳动,同
时作为 “人 +智能机器人”组合中的主观能动者肩负着监控工作流程是否和谐顺畅高效、
智能机器人运转是否正常可控的重要任务,理应从智能机器人创造的价值中获取一定份
2 · ·
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