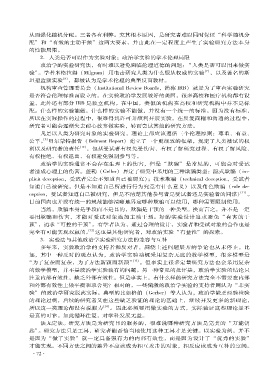Page 64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P. 64
从而强化随机分配。三者各有利弊。究其根本原因,是研究者难以同时保证 “科学随机分
配”和 “有效的主动干预”这两大要素,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实验研究方法本身
的性能局限。
2. 人类是否可以作为实验对象:政治学实验的学术伦理局限
政治学的实验研究法,有时难以避免面临伦理道德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用来做实
验”。学者米格拉姆 ( Milgram)用电击研究人类为什么服从权威的实验 ,以及著名的斯
〔 7〕
坦福监狱实验 ,都被认为是学术伦理的典型反面教材。
〔 8〕
机构审查管理委员会 (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简称 IRB)就是为了审查实验研究
是否符合伦理标准而设立的。在实验政治学发展较好的美国,很多高校和医疗机构都有设
置,此外还有部分 IRB 是独立机构。在中国,类似的机构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并不是标
配。什么样的实验能做,什么样的实验不能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没有标准,
所以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难得到许可并顺利开展实验。在反复商榷和沟通的过程中,
研究者可能会逐渐失去耐心放弃做实验,转而尝试其他的研究方法。
凡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理论上都应该遵循三个伦理原则:尊重、有益、
公平。 贝尔蒙特报告 ( Belmont Report)建立了一个更细致的框架,规定了人类被试的权
〔 9〕
利以及研究者的责任 ,包括受试者有权免受伤害、有权了解研究过程、有权了解风险、
〔 10〕
有权拒绝、有权退出、有权避免强制参与等。
政治学的实验通常不会存在生理上的伤害,但是 “欺骗”是常见的,可能会对受试
者造成心理上的伤害。盖勒 ( Geller)界定了研究中采用的三种欺骗类型:隐式欺骗 ( im
plicit deception,受试者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研究);技术欺骗 ( technical deception,受试者
知道自己被研究,但是不知道自己所进行行为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角色欺骗 ( role de
ception,受试者知道自己被研究,但是不清楚其他参与者是受试者还是实验者的同谋) 。
〔 11〕
目前国内也并没有统一的规范能够清晰地界定哪种欺骗可以使用,哪种需要限制使用。
当然,欺骗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欺骗是干预的一种类型。换而言之,并不是一定
要用欺骗和伤害,才能对受试对象施加主动干预。好的实验设计追求避免 “有害的干
预”,追求 “可控的干预”。有学者认为,通过合理的设计,实验者和受试对象的合作也是
完全有可能实现双赢的。 这也是其他研究者,对政治实验 “有益性”的探索。
〔 12〕
3. 实验法与其他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的兼容与互补
多年来,实验政治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比
如,其中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政治学实验动辄采用复杂无比的数学模型,很多模型是
“为了复杂而复杂,为了方法新颖而新颖” 。但事实上很多定量研究方法也会采用复杂
〔 13〕
的数学模型,并不是政治学实验独有的问题。另一种常见的批评是,政治学实验的结论只
注重内部有效性,缺乏外部有效性。但是事实上,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完全不需要在内部
和外部有效性上做平衡和取舍呢?相对的,一些偏激的政治学实验的支持者则认为 “非实
验”的政治学研究脱离实际。典型的比如格伯 ( Gerber)等人认为,政治学缺乏经验检验
的理论过剩,后续的研究者又在这些缺乏验证的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开发更多的新理论,
所以这一类理论都没有说服力 。因此必须要用做实验的方式,实际验证这些理论是不
〔 14〕
是真的可靠。如此循环往复,对学科发展无益。
法无定法。研究方法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很难说哪种研究方法是完美的 “万能钥
匙”。研究方法只是工具,研究者能否恰当地使用这种工具才是关键。以实验为例,并不
是因为 “做了实验”就一定具备强有力的内部有效性,而是因为设计了 “优秀的实验”
才能实现。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不应该成为相互攻击的对象,相反应该成为互补的空间。
2 ·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