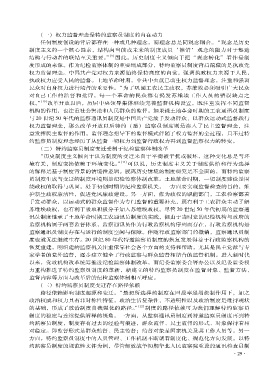Page 30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P. 30
(一)权力监督理念是特约监察员制度的内在动力
任何制度创设的背后都存在一种或几种理念,而理念总是同观念耦合。“观念是历史
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因素,结构向当前或未来的制度成员 ‘推销’观念的能力对于塑造
结构与行动者的联结至关重要。” 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把 “观念转化”看作是制
〔 9〕
度形成的来源。作为纪检监察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约监察员制度背后蕴藏的是执政党
权力监督理念。中国共产党对权力来源始终保持高度的自觉,强调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
执政权力应受人民的监督。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已萌生权力监督理念,注重和强调
民众对自身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性。“为了巩固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
对自己工作的监督和批评。每一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
权。” 改革开放以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完善监督机构设置,既注重发挥不同监督
〔 10〕
机构的作用,也注重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通讯员制度
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监察通讯员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以群众运动式监督践行
权力监督理念,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特约 (邀)监察员制度则是渗入了民主监督理念,注
意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监督理念指导下的监督模式伴随了权力监督的全过程,只不过特
约监察员制度理念经历了从监督一切权力到监督行政权力再到监督监察权力的转变。
(二)特约监察员制度变迁受制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认为制度的变迁来自于平衡被干扰或破坏,这种变化总是与环
境有关,制度变换依赖于环境变化。” 可以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供给和行为选择
〔 11〕
的解释是基于制度背景的情境性逻辑。脱离历史情境的制度研究是不全面的,而特约监察
员制度生成与变迁的制度环境则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土地革命时期,一切制度建设是围
绕政权的取得与巩固。处于初创时期的纪检监察机关,一方面要实现监督检查的目的,维
护新生政权廉洁性,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作为政权的职能部门,工农检察部着
手发动群众,以运动式的群众监督作为专门监督的重要补充,既有利于工农群众主动了解
苏维埃政权,也有利于吸取积极分子加入苏维埃政权。尽管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监察通
讯员制度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践,但由于当时党的纪检机构与政府的
监察机构属于两套监督体系,监察通讯员作为行政监察机构序列而存在,行政监察机构是
监察通讯员制度存在与运行的制度空间与保障。伴随行政监察部门的撤销,监察通讯员制
度也就无法继续生存。20 世纪 80 年代特邀监察员制度的恢复发展得益于行政监察机构的
恢复重建。刚组建的监察机关注重依靠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民主党派与专
家学者的党外监督,逐步建立健全了行政监察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进入新时代
以来,党政机构改革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而纪委监察委合署办公以及纪委监委权
力重构推进了特约监察员制度的革新,新建立的特约监察员制度在监督对象、监督方法、
监督内容等方面与改革后的纪检监察体制相互呼应。
(三)特约监察员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影响制度起源和变迁。“最初所选择的制度在回报率递增机制作用下,加之
政治权威和权力具有非对称性特征,政治生活复杂性、不透明性以及政治制度是维持现状
的基础,形成了政治制度自我强化的路径。” 制度的路径依赖可为我们理解特约监察员
〔 12〕
制度的稳定与连续提供解释的视角。一方面,从监察通讯员制度到特邀监察员制度再到特
约监察员制度,制度存有过去的经验与痕迹,群众监督、民主监督的形式、对象保持着相
对稳定。即监督形式是群众监督、民主监督;监督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另一
方面,特约监察员制度中的人员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朝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特
约监察员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为例,尽管解放战争初期华北人民监察院重设的通讯检查员制
9 ·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