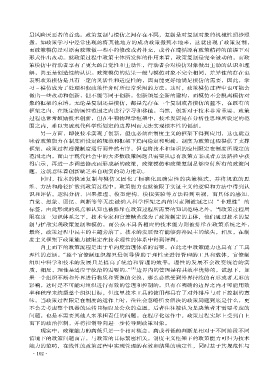Page 103 - 《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
P. 103
量风险厌恶者的首选。政策复制与模仿之间存在不同,复制是对复制对象的机械性照抄照
搬,如政策学习中经常出现的将其他地方的成功政策搬到本地来,这就出现了政策复制,
而政策模仿是对原有政策做一些小的修改或者补充,或者在遵循原有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对
形式作出改动。就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政策复制是完全被动的,而政
策模仿中行动者享有了更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行动者会对模仿对象做出主动的认识和理
解,甚至是创造性的认识。政策模仿的结果一般与模仿对象不完全相同,差异性的存在也
表明政策模仿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因而能更好地满足模仿的需要,因此,学
习 -模仿成为了处理相似政策任务时所经常采用的方法。这时,政策模仿过程中也可能会
做出一些改动和创新,但不能等同于创新。创新须是全新的建构,而模仿不会脱离模仿对
象的框架的束缚。无论是复制还是模仿,都是先存在一个复制或者模仿的蓝本,在既有的
框架之内、在既定的属性范围之内进行学习和移植。当然,创新对于技术非常重要,政策
过程也常常鼓励技术创新,但在牛顿物理学框架中,技术发展是在分析性思维所设定的范
围之内,难以突破现代科学所划定的边界因而无法实现根本性的创新。
另一方面,即使技术实现了创新,但也必须在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得到应用,这也就意
味着政策能力在制度所设定的规范和框架下趋向稳定和明确。制度为政策过程提供了支撑
框架,政策过程遵循制度运行而井然有序,但也将技术和知识的应用限定在制度所规定的
范围之内。而由于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政策问题只需要从已有政策方案或者方法路径中获
得启示,再进一步调整修改而形成新的政策,政策模仿和政策复制足够应付所有的政策问
题,这就意味着创新缺乏来自现实的动力推动。
同时,技术的快速复制与模仿又固化了标准化且确定性的决策模式,并将规范的思
维、方法和路径扩散到政策过程中,政策能力也就被限于实证主义的逻辑和方法中得到认
识和评估。逻辑分析、因果推理、模型建构、模拟实验等方法得到重视,而具体的感知、
直觉、想象、回忆、判断等等无法被纳入科学框架之内的因素则被冠之以 “非理性”的
标签,由此形成的观点和认知也被排斥在政策过程所需要的知识范畴之外。当政策过程局
限在这一知识体系之下,技术专家和官僚精英成为了政策制定的主体,他们通过技术的复
制与扩散实现政策复制和模仿,而公众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则被排斥在政策系统之外,
最终,政策过程中民主的主题旁落了。技术的发展没有能够弥补民主的缺失,相反,在制
度主义框架下政策能力被限定在技术理性的体系中得到评判。
自上而下的政策流程是出于单向度治理体系的需要,在此之中政策能力也具有了工具
理性的意涵。“整个官僚制组织都只是领导借助于理性来进行管理的工具和载体,官僚制
组织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是提高了统治和管理的效率。理性的发展不会改变统治的实
质,相反,理性是适应于统治的需要的。” 边界内的管理是有其效率优势的,试想下,如
〔 4〕
果一个组织不断和外界进行物质和资源的交换,那么必然受到外界持续的有形或者无形的
影响,这时是不可能对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的。只有在明确的边界之内才可能用效
率和秩序来统摄整个组织目标,但这里技术工具的使用都具有了对外排斥与对下控制的意
味。当政策过程限定在制度的运作上时,往往会忽略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到底是什么,更
不会去考虑整个机器的运转目标以及公众的意愿,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决策者才需要考虑的
问题,也是不需要其他人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程序化运作中,政策过程实际上受到自上
而下的政治控制,并将控制导向进一步传导到政策对象。
现实中,政策能力的高低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高或者低的判断是相对于不同阶段不同
情境下的政策问题而言,与政策的目标紧密相关。制度主义框架下的政策能力可归为技术
能力的范畴,在线性的政策过程中实现管理的有效和结果的确定性,同时基于其规范性与
0 · ·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