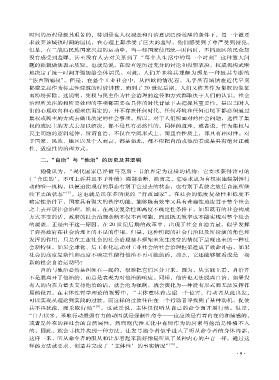Page 9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P. 9
时间的历程是极其艰苦的,特别是在人权观念和自治意识已经觉醒的条件下,每一个被要
求放弃该城镇时间的居民,在心理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羞辱,他们感受到了尊严受到侵犯。
但是,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兴起的运动中,当一些国家使用统一时间时,不同地区的民众却
没有感受到羞辱,甚至没有人去对关系到了 “每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这种重大问
题的独裁做法表示质疑。也就是说,在没有经历过充分的讨论和投票表决,权威机构武断
地决定了统一时间并强加给全体居民。对此,人们并未将其理解为那是一种极其专断的
“法西斯霸权”。但是,在整个工业社会中,从西欧的情况看,几乎所有城镇在近代早期
都建立起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时钟钟楼,而到了 20 世纪后期,人们又将其作为集权的象征
而纷纷拆除。这说明,集权与民主作为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都取决于人们的认识,社会
治理所关注的和所要处理的事项都需要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去把握其重要性,是以当时人
们的心理取向和心理聚焦而定的,并不存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和任何语境下都必须通过
集权或民主的方式去做出决定的社会事项。所以,对于人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选择了集
权的或民主的方式去加以解决,都不是具有必然性的。同样的道理,或者说,作为集权与
民主问题的逻辑延伸,所谓自治,不仅在空间形式上,而且在性质上,都具有相对性。对
于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个人而言,都是如此,都不应把自治或他治看成是具有绝对正确
性、适应性的治理方式。
二、“自治”与 “他治”的历史及其逻辑
鲍曼认为,“现代国家已经被马克斯·韦伯界定为这样的机构:它要求获得许可的
(‘合法的’,不可上诉并且不予补偿)强制垄断,换言之,它要求成为有权实施强制性行
动的唯一机构,以便迫使现存的事态有别于它过去的状态,也有别于若使之放任自流所继
续下去的状态” 。这也就是沃尔多所说的 “行政国家”。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
〔 8〕
确定性条件下,国家具有强大的秩序功能,能够既有效率又具有普遍性地凌驾于整个社会
之上去开展社会治理。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既有的社会构成
方式不变的话,政府的社会治理垄断不仅不再可能,而且既无效率也不能实现对整个社会
的覆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 20 世纪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社会自治力量,似乎发挥
了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不足的作用。但是,这种所谓的社会自治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和
发挥的作用,只是在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基本框架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呈现出来的一种社
会新特征。如果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对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框架造成了致命冲击,如果
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他治不再可能的话,那么,它还能够被看成是一场
新的社会自治运动吗?
自治与他治必然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因为,从实践上看,自治并
不是脱离开了他治的,而总是表现为对他治的响应。同样,他治也无法脱离自治,如果没
有人的内在力量去支持他治的话,就会沦为强制,就会演化为一种徒有形式而无法发挥作
用的设置。在主体性哲学理论的视野中,“主体意味着占据一个位置,行动者从此出发,
可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而这样的过渡往往在一个行动者寻找到了某种动机,促使
其不再犹豫,而采取行动” 。也就是说,主体仅仅听从自己的命令而开展行动。但是,
〔 9〕
“自古以来,采取行动最强有力的动因就是强制性命令———这应该是有着内在的和情感的,
或者是外在的和社会的自然属性。然而现代性文化中有所作为的因素与他治是格格不入
的,因此,就会寻找并找到一种方法,让发号施令者似乎进入了听从命令者的身体内部,
这样一来,听从命令者的服从和让步看起来就好像是听从了某种内心的声音一样。通过这
样的方法就要求、创造并完成了 ‘主体性’的事实情况” 。
〔 10〕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