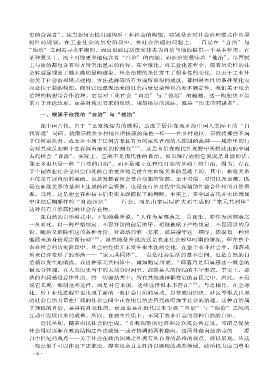Page 6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P. 6
史的合谋者”,应当如何去提出建构后工业社会的构想,特别是去对社会治理模式作出原
则性的规划。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一直是在 “自治”与
“他治”之间去寻求平衡的,而且也通过制度安排去为自治与他治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在
某种意义上,民主可能更多地包含着 “自治”的内涵,而法治则意味着 “他治”,尽管民
主与法治都包含着对方所突出显示的内容。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历史性的社
会转型显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迹象,社会治理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于工业社
会关于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法选择等所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因根本性的条件变化而
应让位于新的构想。面对已经显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我们关于社会
治理的构想是合作治理,它是对工业社会 “自治”与 “他治”的超越。这一构想决不是
来自于理论致思,而是对现实要求的反映,用昂格尔的说法,就是 “历史的同谋者”。
一、根源于自我的 “自治”与 “他治”
在中国古代,由于 “皇室统辖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的 ‘自
我管理’局面。就像宗族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在乡村地区,宗族将那些不属
于任何宗族者,或至少不属于任何古老且有力的宗族者都纳入控制的范围———城市里的行
会对其成员的整个生存握有绝对的控制权” 。这是韦伯在现代性视野中所解读出的中国
〔 3〕
古代社会 “自治”,实际上,它决不是现代性的自治。如果强行地把它说成是自治的话,
那至多也只是一种 “自然的自治”,而不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上的自治。因为,存在
于中国农业社会皇权空白处的自治更多地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其中,血缘关系
不仅是开展自治的基础,也是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的资源。至于习俗、习惯以及道德,既
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生成的社会资源,也是在自治过程中发挥辅助性整合作用的自然资
源。当然,这是建立在相信韦伯史实无误前提下的判断,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并未出现如
中世纪后期那样的 “自治组织”———行会,而是由家层层扩大而生成的 “家元共同体”
这种具有自然属性的社会存在物。
在自然的自治模式中,正如鲍曼所说,“人作为某部落之一员而生,亦作为该部落之
一员而死,以一种严格规定、不容异议的前后顺序,相继被赋予严格规定、不容商议的身
份,随后又解除相应的各种身份。对部落的惟一要求,就是遵守这一顺序,依据每一种相
继而来的身份规定而行动” 。虽然鲍曼所说的还是农业社会较早时期的情况,但在整个
〔 4〕
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整个农业社会中,部落或
后来已经变形了的部落——— “家元共同体”,一直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自然的自
治赖以发生的前提。在这种家元共同体中,诚如鲍曼所说,“部落乃是归属感这一概念的
最充分体现,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部落是人的抟结的主导形式。事实上,部
落的归属感是总体性的,将一切囊括其中;所有其他选择都在它的盲区之中,因此,不是
说它无视、抑制这些选择,而是对它来说,这些选择根本不存在” 。与之相比,在全球
〔 5〕
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了新的一波社会自治的运动,以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形式出现
的社会自治力量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正在用自治去替代政府加予社会的治理。这种自治属
于理性的自治,是具有自觉性的,而且也是在近代以来全部 “自治”与 “他治”之间的
互动中发展出来的成果。所以,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农业社会的那种自然的自治。
近代早期,随着市民社会的生成,“自我调整的经济和公众或公共意见,可谓是促使
社会得以逐渐在政治结构之外达致统一或者协调的两种路向。这两种路向使洛克的———源
自中世纪的观点———关于社会在政治领域之外拥有其自身的品格的观点,得以展现。从这
一观点似乎可以作出下述推论,即在社会自主性得以展现的那些领域,政治权力应当尊重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