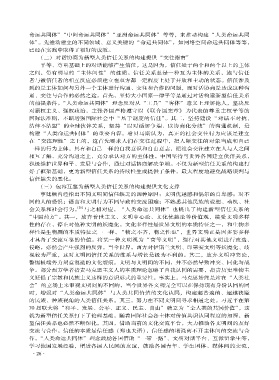Page 26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P. 26
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等,来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
体”。先推动建立的不同领域、意义关键的 “命运共同体”,如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等,
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二)对话协商为新型人类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 “交往指南”
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对话能够产生信任。这是因为,信任处于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主体
之间,带有明显的 “主体间性”的性质。信任关系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施与信任
者与被信任者的相互反应必须建立在双方都一定程度上处于开放和主动的状态。信任涉及
到的是主体如何与另外一个主体进行沟通、交往和合作的问题,而对话协商是达成这种沟
通、交往与合作的必然之途。首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通过对话构建新型信任关系
的前提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从 “工具”“客体”意义上理解他人,坚决反
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张各国严格遵守以 《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尊重主权平等的
国际法准则,不断增强国际社会中 “基于制度的信任”。其二,坚持建设 “对话不对抗、
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坚持 “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的沟通机制,是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交往行为应该是建立
在 “交往理性”之上的,这首先要求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把人际交往的对象当成和自己
一样的行为主体,具有和自己一样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把社会交往建立在人与人之间
相互了解、充分沟通之上,充分承认对方的主体性。中国坚持与世界各国建立伙伴关系,
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不仅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打
好了框架基础,更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持续性生成提供了条件,最大程度地避免战略误判与
信任缺失的恶化。
(三)包容互鉴为新型人类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文化支撑
亨廷顿曾经指出不同文明间信任缺乏的四种原因:文明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对不
同的人的恐惧;语言和文明行为不同导致的交流困难;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
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与之相对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出了构建新型信任关系的
〔 20〕
“中国药方”。其一,放弃普世主义、文明中心论、文化优越论等价值观,接受文明多样
性的存在,停止对他种文明的妖魔化。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和生物多
样性是生物圈的本质特征之一一样。“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世界文明正是因多姿多样
才具备了交流互鉴的价值。将某一种文明视为 “高等文明”,强行对其他文明进行改造、
侵略,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当今世界,西方对伊斯兰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妖魔化、歧
视较为严重,这对文明间信任关系的维系与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其二,放弃文明冲突论,
警惕极端势力刻意制造的文化裂痕。文明与文明间的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同化与战
争。部分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忽略了自我认同的需要,指责历史唯物主
义贬低了宗教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式的重要性。事实上,马克思始终是站在 “人类社
会”的立场上来审视文明间的不同的,当今世界各文明完全可以在保持现有身份认同的同
时,增强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认同,构建起普遍的、超越狭隘
的民族、种族视角的人类信任关系。其三,努力在不同文明间寻求相通之处。习近平在第
70 届联大将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确立为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
就为新型信任关系打下了伦理基础。随着国际社会各主体对价值共识认同程度的加深,新
型信任关系也必然不断深化。其四,借助当前的文化交流平台,大力推动各文明间的友好
交流与合作。信任的本质是信任感 (郑也夫语),信任感的增强离不开主体间的交流与合
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各国借助 “一带一路”、文明对话平台、互派留学生等,
学习他国发展经验,增进各国人民间的友谊,鼓励各国青年、学生团体、媒体间的交流,
6 ·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