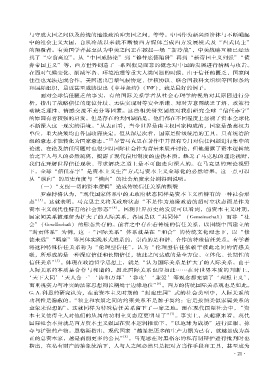Page 21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P. 21
与守成大国之间以及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国之间,等等。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与不断崛起
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自从冷战以来就不断被西方媒体当成西方发展模式及 “西式民主”
的颠覆者。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中美之间正在掀起一场 “新冷战”,中美战略互疑已经达
到了 “空前高度”。从 “中国威胁论”到 “修昔底德陷阱”再到 “新帝国主义列强”“债
券帝国主义”等,西方世界创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猜测与攻击。
在面对气候变化、削减军备、环境治理等重大人类问题的时候,由于信任的匮乏,国家间
往往也无法达成合作。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条约
和国际组织,最近甚至威胁退出 《中导条约》( INF),就是最好的例子。
面对全球信任匮乏的事实,有的国际关系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其原因进行分
析,指出了战略信任的定位分歧、无法实现对等安全承诺、对对方意图缺乏了解、政策行
动缺乏理性、情感交流不充分等因素。这些相关研究固然对我们研究全球 “信任赤字”
的原因有着较强的启发,但是存在的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资本全球化
不断深入这一现实的语境。“从表面看,当今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是最高权力
单位,重大决策均由各国政府决定。但从深层次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统治阶
级的意志才能转化为国家意志。” 尽管马克思在著作中并没有专门对信任问题进行集中的
〔 2〕
论述,在论及信任问题时也很少以国际社会作为背景来展开讨论,但他揭露了资本逻辑统
治之下人与人的必然疏离,揭露了现代信用制度的虚伪本质。缺乏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
我们在理解世界信任现状、寻求解决之道上是不可能走向深入的。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
下,全球 “信任赤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可以
从 “纵向”的历史角度与 “横向”的社会角度来分别得到说明。
(一)“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造成传统信任关系的撕裂
罗森博格认为,“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同样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形
态” 。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将无政府状态 “不是作为地缘政治的超时空状态而是作为
〔 3〕
资本主义现代性特有的社会形态” 。回溯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前资本主义时期,
〔 4〕
国家间关系被理解为扩大了的人际关系,各国是以 “共同体” ( Gemeinschaft)而非 “社
会”( Gesellschaft)的形态共存的。前者之中存在着传统的信任关系,以围绕中国建立的
“封贡体系”为例,这一 “国际关系”体系就是在 “和合”的传统文化理念下,以 “修
德来远”“羁縻”等具体实践形式维系的,崇尚的是和谐、合作的特殊信任关系。有学者
将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称为 “伦理型信任”,认为 “伦理型信任依赖于彼此之间的情感关
联,所形成的是一种深度信任和长期信任,彼此之间达成的是全方位、立体化、长期性的
信任关系” 。体现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就是 “认为国际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由于
〔 5〕
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也应如此……在对世界本质的判断上,
‘天下大同’‘天人合一’ ‘协和万邦’ ‘非攻’ ‘兼爱’等观念都充满了 ‘理想主义’,
而重视实力与冲突的法家思想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西方的传统国际关系观也是如此。
〔 6〕
G. A.科恩的研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 “封建庄园”式的社会类型中,人际关系的
功利性是隐蔽的,“领主和农奴之间的约束关系不是源于契约:它是按照类似家属关系的
意象来设想的”。这就同样为特殊信任关系留下了一席之地。而在现代国际社会中,“资
本主义使得主人对他们的从属的功利主义态度更明显了” 。事实上,从起源来看,现代
〔 7〕
国际社会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资本逻辑推动下,“以地球为战场”进行征服、掠
夺与扩张的产物。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 “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
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私有制辩护进行批判时也
〔 8〕
指出,在私有财产的抽象统治下,人与人之间必然只是把对方当作手段和工具,甚至成为
1 ·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