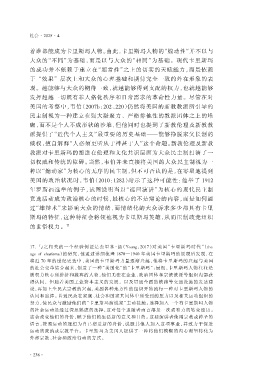Page 245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245
社会·2025·4
着谁都能成为卡里斯玛人物。由此,卡里斯玛人物的“煽动性”并不以与
大众的“不同”为基础,而是以与大众的“相同”为基础。 现代卡里斯玛
的成功并不依赖于建立在“超常性”之上的切实的天赋能力,而是依赖
于“效果” 层次上和大众的心理基础和期待完全一致的外在形象的表
现。 越能够与大众的期待一致,就越能够得到支配的权力,也就越能够
发挥超越一切既有非人格化秩序和日常需求的革命性力量。 尽管在对
美国的考察中,韦伯(2007b:202、220)仍然将美国的新教教派所引导的
民主制视为一种建立在强大凝聚力、 严格排他性的教派团体之上的堆
砌,而不是个人不成形状的沙堆,但他同时也提到了新教伦理及新教教
派提供了“近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基础———能够挣脱家父长制的
威权,擅自解释“人必须更听从于神甚于人”这个命题。新教伦理及新教
教派对卡里斯玛的塑造在伦理和文化共识层面为大众民主制扫清了一
切权威和传统的障碍。 当然,韦伯并未直接将美国的大众民主制视为一
种以“煽动家”为核心的无序的民主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零星地提到
美国的政治状况时,韦伯(2010:1282)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他举了 1912
年罗斯福选举的例子,试图说明当以“巡回演讲”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
竞选活动成为政治核心的时候,最核心的不是辩论的内容,而是如何通
过“雄辩术”来影响大众的情绪,而情绪化的大众诉求多少都具有卡里
斯玛的特征,这种特征会将领袖视为卡里斯玛英雄,从而压制政党组织
的世俗权力。 17
17. 与之相关 的一个 经验例 证是杰 里米·扬(Young,2017)对 美 国“卡 里 斯 玛 时 代 ”(the
age of charisma)的研究,他通过详细梳理 1870—1940 年美国卡里斯玛的展现后发现,在
将近 70 年的世纪更迭中,美国的卡里斯玛力量逐渐兴起,他将卡里斯玛的兴起与美国
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美国化”的“卡里斯玛”:最初,卡里斯玛人物往往是
被权力核心所排挤和抛弃的人物,他们无法在企业、政治团体和宗教教派等组织内部获
得认同, 但随着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以及贯通全国的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发达建
设,再加上全民式宗教的兴起,美国各种地方性的组织开始流行一种对卡里斯玛人物的
认同和追捧。 普通民众在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体中所受到的压力以及相关运动组织的
努力,使民众与激励他们的“卡里斯玛演说家”主动接触。 选择加入一个有卡里斯玛人物
的社会运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这对每个追随者而言都是一次强有力的转变经历。
这会改变他们的身份,赋予他们的生活新的意义和目的。 这些演讲者使用宗教或神圣的
语言,按照运动的理想为自己塑造新的身份,说服其他人加入这项事业,并致力于促进
运动的政治或宗教平台。 卡里斯玛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将他们模糊的内心渴望转化为
外部宗教、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方式。
· 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