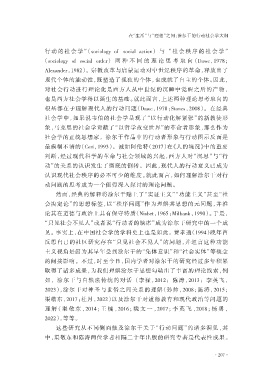Page 214 - 《社会》2025年第2期
P. 214
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涂尔干的行动社会学大纲
行 动 的 社 会 学 ”(sociology of social action) 与 “社 会 秩 序 的 社 会 学 ”
( sociology of social order) 两 种 不 同 的 理 论 思 考 取 向(Dawe,1978;
Alexander,1982)。 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秩序的革命,释放出了
现代个体的能动性,既塑造了孤独的个体,也成就了自主的个体。因此,
对社会行动进行理论化是西方人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觉醒之后的产物,
也是西方社会学得以诞生的基础。 就此而言,上述两种理论思考取向的
根基都在于理解现代人的行动问题( Dawe,1978;Stones,2008)。 在经典
社会学中,如果说韦伯的社会学呈现了“以行动化解紧张”的新教徒形
象,马克思的社会学贡献了“以哲学改变世界”的革命者形象,那么作为
社会学的正统思想家, 涂尔干作品中的行动者形象与行动图示反而是
最模糊不清的(Ceri,1993)。 诚如阿伦特(2017)在《人的境况》中的重要
判断,经过现代科学的革命与社会领域的兴起,西方人对“沉思”与“行
动”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倒转。 因此,现代人的行动意义已成为
认识现代社会秩序的必不可少的维度。 就此而言,如何理解涂尔干对行
动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然而,经典的解释将涂尔干贴上了“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甚至“社
会决定论”的思想标签,以“秩序问题”作为理解其思想的元问题,并推
论其在道德与政治上具有保守特质( Nisbet,1965;Milbank,1990)。 于是,
“只见社会不见人”或者说“行动者的缺席”成为涂尔干研究中的一个成
见。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上也是如此。 费孝通(1994)晚年曾
反思自己的社区研究存在“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问题,并坦言这种功能
主义视角是因为其早年受到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实体”等概念
的间接影响。 不过,时至今日,国内学者对涂尔干的研究经过多年积累
取得了诸多成果,为我们理解涂尔干思想勾勒出了丰富的理论线索,例
如, 涂尔干与自然法传统的对话 (李猛,2012; 陈涛,2013; 李英飞,
2023),涂尔干对神圣与世俗之间关系的理解(孙帅,2008;陈涛,2015;
渠敬东,2017;杜月,2022)以及涂尔干对道德教育和现代政治等问题的
理 解(渠 敬 东 ,2014; 王 楠 ,2016; 魏 文 一 ,2017; 李 英 飞 ,2018; 杨 勇 ,
2022),等等。
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触及涂尔干关于“行动问题”的诸多洞见,其
中,渠敬东和陈涛两位学者相隔二十年出版的研究专著是代表性成果。
·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