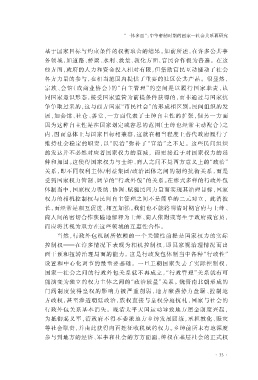Page 40 - 《社会》2022年第5期
P. 40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基于国家目标与约束条件的权衡取舍的结果。 如前所述,在许多公共事
务领域,如道路、桥梁、水利、救荒、教化方面,官民合作极为普遍。 在这
些方面,政府的人力和资金投入相对有限,但借助官民互动撬动了社会
各方力量的参与,在相当范围内提供了重要的社区公共产品。 很显然,
宗族、会馆(或商业协会)的“自主管理”的空间是以履行国家职责,认
同国家意识形态,接受国家监管为前提条件获得的,而非通过与国家抗
争争取过来的,这与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形成相区别。民间组织的发
展,如会馆、社仓、善堂,一方面代表了士绅自主性的扩张,但另一方面
因为这种自主性是在国家划定或容忍的范围(士绅也经常主动配合)之
内,因而总体上与国家目标相兼容,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政府履行了
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以“民治”弥补了“官治”之不足。 这些民间组织
的发达并不必然对应着国家权力的衰减, 而更接近于对国家权力的延
伸和加固。这使得国家权力与士绅、商人之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
关系,即不同权利主体/利益集团/政治团体之间的制约抗衡关系,而是
受到国家权力管制、调节的“行政外包”的关系。在形式多样的行政外包
体制当中,国家权力吸纳、协调、赋能民间力量而实现其治理目标,国家
权力的相机控制权与民间自主管理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此消彼
长,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相互加强。我们也不能将明清时期官府与士绅、
商人间的密切合作狭隘地解释为士绅、商人依附或寄生于政府或官员,
而应将其视为双方在这些领域的互惠性合作。
当然,行政外包机制所依赖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是国家权力的实际
控制权———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相机控制权,即国家视治理情况而出
面干预和扭转治理局面的能力。 这是行政发包体制当中各种“行政性”
设置和中心化调节的最重要基础。 一旦王朝国家失去了实际控制权,
国家—社会之间的行政外包关系就不再成立,“行政管理”关系就有可
能演变为独立的权力主体之间的“政治较量”关系。 魏晋南北朝形成的
门阀制度使得皇权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地方豪强势力盘踞、控制地
方政权,甚至渗透朝廷政治,族权直接与皇权分庭抗礼,国家与社会的
行政外包关系基本消失。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地方厘金制度兴起,
为抵御起义军,清政府不得不委派地方乡绅发展团练,承担教化、赈灾
等社会职责,并由此获得向百姓征收税赋的权力。 乡绅前所未有地深度
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军事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绅权在基层社会的正式权
·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