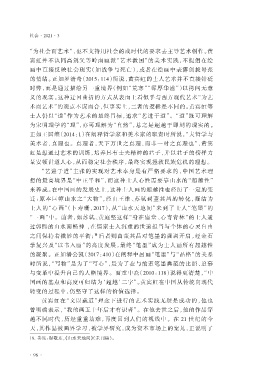Page 103 - 《社会》2021年第3期
P. 103
社会·2021·3
“为社会而艺术”,也不支持用社会的或时代的要求去主导艺术创作。黄
宾虹并不认同高剑父等岭南画派“艺术救国”的美术实践,不提倡在绘
画中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如战争与死亡),或者在绘画中表露剑拔弩张
的情绪。 正如罗清奇( 2015:114)所说,黄宾虹的士人艺术并不直接针砭
时弊,而是通过描绘另一重境界(例如“荒寒”“浑厚华滋”)以拷问无意
义的现实。 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与西方现代艺术“为艺
术而艺术”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事实上,二者的逻辑是不同的。黄宾虹等
士人仍以“道”作为艺术的最终目标,追求“艺进于道”。“道”既可理解
为宋明理学的“理”,亦可理解为“自然”,总之是超越于即刻的现实的。
正如王国维( 2014:1)在阐释哲学家和美术家的职责时所说,“夫哲学与
美术者,真理也。 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黄宾
虹是想通过艺术的训练,培养具有士夫精神的君子,并以君子的榜样力
量安顿世道人心,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最终实现拯救民族危机的理想。
“艺进于道”主张的实现对艺术本身是有严格要求的,中国艺术理
想的最高境界是“中正平和”,而这种士人心性需要靠山水的“超越性”
来养成。 在中国画的发展史上,这种士人画的超越性也经历了一定的变
迁:原本巨幛山水之“大物”,经由王维、苏轼到董其昌的转化,凝结为
士人的“心画”(卜寿珊,2017),从“山水天地间”来到了士人“笔墨”的
“一画”中。 前者,如苏轼、黄庭坚这样“身在庙堂、心寄青林”的士人通
过郭熙的山水而畅神 ,在儒家士人沉重的世道担当与个体的心灵自由
18
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后者则由董其昌对笔墨的强调开启,经金石
学复兴及“以书入画”的高度发展,最终“笔墨”成为士人画所有超越性
的凝聚。 正如潘公凯(2017:410)在阐释中国画“笔墨”与“品格”的关系
时所说,“写物”是为了“写心”,是为了在与前辈笔墨典范的比照、追慕
与变革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 而童中焘(2010:118)说得更清楚,“中
国画的基点和高度可归结为‘超越’二字”。黄宾虹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
转变的过程中,仍坚守了这样的价值选择。
黄宾虹在“ 文以载道”理念下进行的艺术实践无疑是成功的,他也
曾明确表示,“我的画五十年后才有识者”。 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穿
越不同时代,历经重重劫难,再度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在 21 世纪的今
天,其作品被画界学习,被学界研究,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宠儿,正说明了
18. 参见:渠敬东,《山水天地间》(未刊稿)。
· 96 ·